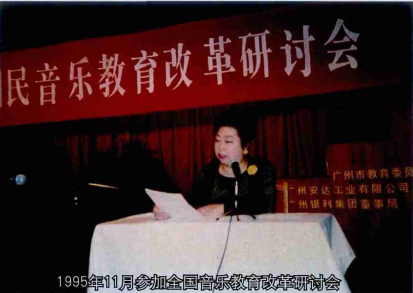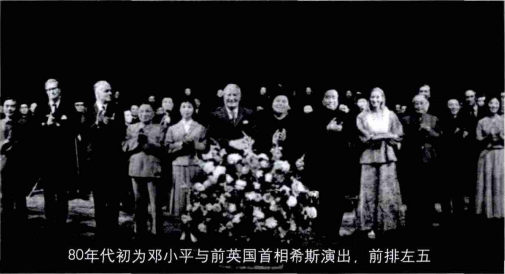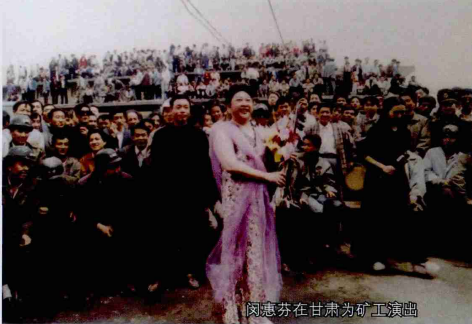十余年前,我写过一篇《一件乐器和一个世纪-二胡艺术百年观》的长文。写作的出发点是把这件旧时代地位低下的民间乐器放在20世纪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全面转型的背景下,追溯它为什么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历史进展?以及为此献身的几代二胡艺术家在创作、表演、教育传承和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哪些贡献?借以探求一门器乐艺术与一个变革时代之间的相互关联。然而,就在这一领域在近十余年间继续大步向前、收获了更多优秀的二胡作品、培养了更新一批二胡演奏家、出版了更动听的二胡唱片之际,我们却失去了与二胡相伴六十年、驰骋二胡舞台五十年、深受千千万万二胡人钟爱、被西方媒体誉为“世界伟大的弦乐演奏家之一”、令我们十分尊敬的闵惠芬老师,2014年5月12日上午十时,她永远离开了我们。
她的走,结束了二胡艺术的一个时代,但留下了属于她的“时代琴音”,让我们反复听赏,从中汲取教益;她的走,同时也留下一系列话题和一份宝贵的遗产:在中国民族器乐艺术的现代演进历程中,一位伟大的演奏家对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演奏艺术具有何种意义?两者存在哪些相互补益、促进和提升的关系?当代的优秀二胡名家们应该向闵惠芬学习什么?等等。
于是,闵惠芬与20世纪二胡艺术就成为我本人继“一件乐器与一个世纪”之后自然引出的一个新论题。我想,不仅是我自己,这也是二胡界同仁应当认真思考并予以回答的问题。这里既包含了我们对闵惠芬二胡艺术历史贡献的总结,也有我们从“闵惠芬精神”中获得激励、动力并争取二胡艺术有更大发展格局的种种抉择。
一
二胡作为20世纪才成长起来的一门独奏艺术,闵惠芬之前,已经有前半个世纪的周少梅、刘天华、阿炳、蒋风之、陈振铎、刘北茂,1950年代以后的张锐、孙文明、张韶、王乙、项祖英,以及略早于她的蒋巽风、鲁日融、黄海怀、汤良德、王国潼等二胡艺术家出现。无疑,由这样前后三代人组成的现代二胡艺术阵容已经十分壮观,除了周少梅、刘天华、阿炳在1950年代之前先后离世外,其他各位在1952年至1962年间,不是导师,就是青年才俊,大家齐心努力把这门演奏艺术推向它的第一个历史高峰1963年的全国二胡比赛。谁都没有想到,一次比赛竟然涌现了十几位优秀的演奏家,十几首二胡新作和多种多样的技艺风格。更没有想到的是,大赛的第一名是不满十八岁的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女生闵惠芬。
很显然,这一轰动全国的荣誉成为青年闵惠芬艺术生命的新起点。那么,她如何对待这份荣誉?
如何理解这个“新起点”呢?无论从以往的报道、访谈中,还是在研究文献中,我们都没有看到相关的记录。即使在我2011年3月17日两个多小时对她的专访中,她也几乎一字未提。不仅未提1963年的比赛,就连此后的许许多多的“殊荣”也未着一言。而谈论最多的,反倒是她终其一生都对中国民间音乐丝毫不减的眷恋,是她对每个阶段教过她、没教过她的前辈老师的敬重、怀念和感激,以及她在数十年演奏生涯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艺术观,等等。我想,以上三点也许正是闵惠芬几十年来克服重重艰辛、最终登上当代二胡演奏艺术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许也是我们“解读”闵惠芬二胡演奏艺术内涵的一个新视域。我当时就强烈地感受到,在这位大演奏家心里,哪个是目标如一的人生追求,哪个是可以轻看的“身外之物”,她在年轻时代就已“拎”得很清了。
她告诉我,5岁以前她生活在苏南宜兴乡间的一个很小的村落里,但乡间的各种“声音”却让她十分难忘:算命盲人的“笛声”、卖牙糖小贩的叫卖声、老太太拜佛的“诵经声”、道士们演奏的“十番锣鼓”庙会上的百人“丝竹乐”演奏声、乞讨者的“春调” “哭丧婆”们逼真的“代哭”声、妈妈为宣传婚姻法编唱的小调、南下干部唱的北方小曲以及在电影《陕北牧歌》里听到的《崖畔上开花》,当然,还有她的“爹爹”闵季骞先生每次回家为她演奏的二胡、琵琶、笛子音乐等等,对这些六十多年前“乡下的声音”,她不但记在心里,而且张口就唱,兴趣浓烈。也许,我们幼时也听到类似的歌唱或演奏,但对于闵惠芬而言这些流入心底的“乡音”却别有一番滋味。依照她的看法,正是因为有这些“声音记忆”才让她在进入专业院校以后,几乎对所有的民间音乐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和兴趣,以至看了红线女的《昭君出塞》就立即移到二胡上拉,听了隔壁琴房郭鹰先生给学生教潮州筝曲《寒鸦戏水》就拿上二胡去助奏。我以为,对中国民间音乐这种生了“根”一般的痴迷、尊重、投入才是她1963年的那个“新起点”的“元点”。有了这份挚爱,才让她有了从不放弃的执着,也才有了发誓要把民间音乐的精微一点点注入自己演奏艺术之中的崇高目标。所以,她认为自己获奖的原因之一是自幼受到民间音乐的熏淘浸染。为此,她进入大学后,向民间音乐学得更起劲了。
她的另一个人格“坚守”就是对前辈、老师们艺术造诣的尊重、敬仰。她很早就学会了《二泉映月》和《江河水》这两首绝世名作,而且经常登台表演。但在1972年得到一张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老唱片后,竟然用了半年的时间反复听、反复琢磨,尽力发现阿炳技艺的真谛,寻找自身的不足。如此这般,才确立了自己演奏该曲的风骨韵味,并在二胡界称誉数十年。同样,《江河水》早就是她的保留曲目,但她从未自满,直到1973年有机会见到演奏原曲的双管演奏家谷兴善,立即向他求教,内心流露的喜悦有如僧人取到了“真经”。经过多年打磨,她演奏的《江河水》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琴心合一、感人至深之至境。也才有小泽征尔在1977年听罢演奏的感慨:“拉出了人间悲切,听起来使人痛彻肺腑!”不仅如此,在我们那天的长谈中,她先后道出十几位曾经教过她的老师:二人台艺术家周治家(艺名“邋蹋地”)、张爱兵(艺名“吹破天”),沪剧艺术家吴景德、许国华,婺剧艺术家张小牛,民歌老师江明惇,主课老师王乙、陆修棠,同行前辈张韶,京剧艺术家李慕良等,以至教过她一阵四胡的同学陈大灿,她都要没有遗漏。一个艺术家如果不在内心保持这样一种“尊师重道”的圣洁之情,要获得成功恐怕很难。
其三,闵惠芬有她本人明确而朴素的表演艺术观。对于自己的演奏,每曲每句乃至每个音符都要求极高,几近严酷,表现出高度的专业、敬业精神。但对于听众她却一律视为亲人、朋友、知音,从不以名家、大家自居。她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乐要走进寻常百姓家”。同时加上一句:“无论在山沟里还是在大剧场,国内还是国外,你都要对听众有一份爱。”而在舞台上,“如果你的演奏人情味少了,那你的音乐就和中华大地的大好河山不相匹配了”。“寻常百姓”“人情味”,不过寥寥几个字却道出她对艺术、对听众的真情爱心。话虽说的直白,却有值得所有表演艺术家三思的真理性。
二
闵惠芬8岁开始随闵季骞先生学习二胡,至今已逾一个甲子自1963年获奖,到今年2月生病住院前,她一直活跃于舞台,以职业演奏家的身份在弓弦间拼搏砥砺整整五十年,为当代二胡艺术的全面推进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她作为女性二胡演奏家,不仅改写了这门演奏艺术的性别史,并为此后大批巾帼从事这一事业赢得了不容忽视的地位和尊严;她的舞台生涯时间之长、推出新作之多,演绎作品之精、个人风格之醇、在听众中的影响之大,实为当今二胡领域第一人。
闵惠芬对20世纪二胡艺术最重要的贡献无疑是她完美精致的演奏。五十年间,她先后出版音响、音像专辑共二十余部,这些专辑包括了刘天华、阿炳、刘文金以及古曲、筝曲、歌剧、昆曲、京剧及地方戏唱腔移植作品共六十多首”,至于在舞台上演奏的作品已经无法计算。所演作品的体裁和乐队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独奏、协奏、重奏叙事曲、协奏曲、二胡与乐队;民族管弦乐队、西洋管弦乐队、京剧乐队、潮剧、越剧乐队等。其中,功劳卓著、影响最大的就是在1980一1994年十余年间,她先后首演的四部大型二胡新作,即《新婚别》(张晓峰、朱晓谷曲,1980年,上海)、《长城随想》(刘文金曲,1982年,上海)、《第一二胡协奏曲》(关遒忠曲,1989年,香港)和《夜深沉》(刘念劬曲,1994年,上海)。
《新婚别》之前,从20世纪初到1979年,二胡领域至少有了百余首脍炙人口的佳作,但全部是十多分钟左右的短篇。《新婚别》两位作者将篇幅扩展至16分钟,又是以唐代大诗人杜甫同名诗篇的内容作底本,通过三个各具鲜明个性的段落叙咏了一千多年前的悲剧故事。加上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协奏,使该作在内容的戏剧冲突、音乐的叙事容量以及结构内涵方面均与此前的作品划开明确的界限,堪称20世纪二胡音乐的第一部大型作品。经闵惠芬的出色演绎,在1980代初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也成为闵惠芬本人经常演奏的曲目。同时,它也可以看作是两年以后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出现的前奏。
刘文金四个乐章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的创作、演出是20世纪二胡界甚至是中国民族音乐领域的一件划时代大事,也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作曲家和一位杰出的二胡演奏家完美合作的一件盛事。早在酝酿期间他们就有过较深入的交流,作曲家进入创作以后“预约”的首演者恰好也是闵惠芬,由此也成为“长城”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全曲四个乐章,长度超过28分钟。作曲家借长城的伟岸、雄浑咏颂中华民族尚新、自强、坚韧的伟大精神。作品首演至今三十余年来,获奖多,评论更多,而所有评论均为正面的赞誉。表达了社会大众对这首世纪名作的充分肯定。我还清楚记得1982年年底“长城”在北京红塔礼堂演出的空前盛况。音乐刚一结束,场内就沸涌如潮,观众为作品中的恢宏气度、长大构思、新颖语汇所震撼,也为闵惠芬驾驭大型作品的判断力、丰富经验和精湛演绎所折服。她曾对我说过自己处理一首新作品的心理思绪:“我自己的音乐风格有那么一种天生的大气,不嗲不粘,爽快果断。一个有经验的演奏家处理乐曲要先立大局,自我感觉是诗人、歌手、大元帅,以‘小操作’而求‘大境界’”2。这是对自己数十年舞台实践体验的高度概括,也是对音乐艺术“二度创作”中演奏家与作品关系的精确把握。演奏家当然要尊重原作、体会原作的内在精神和技术要求。但这只是“二度创作”的前提,一旦进入表演就应该是舞台上“主角”,以自己的技艺、理解将作品表达到一种极致。鉴于此,她所谓“诗人”、“歌手”、、“大元帅”的比喻,我觉得是恰当而又准确的。关逎忠《第一二胡协奏曲》的首演是在“长城”发表的6年之后,作曲家采用西方标准的“协奏曲”规格写成此曲。三个乐章分别为奏鸣曲式、三部曲式和回旋奏鸣曲式。独奏部分用了难度很大、倾向于“现代”乐思的旋律语汇,与闵惠芬一向熟悉的技法语言有较大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她在此前身罹恶疾,多次手术、多次化疗,身心遭遇极大的摧残。大病初愈就“啃”这块“硬骨头”,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多大的毅力,可想而知。但她同样出色、圆满地完成了首演。多年后回忆往事,她仍然坚定地表示:与香港中乐团合作演奏《第一二胡协奏曲》,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超越,最后是我胜利了。如果说,“长城”首演是一桩文化辉煌,《第一二胡协奏曲》的首演则是艺术家的精神奇迹。
5年以后,闵惠芬又在上海首演了时长半个小时、三个乐章的二胡协奏曲《夜深沉》。这也是老同学刘念劬专门为她创作的。借用古典戏曲、音乐中的一个十分普遍的主题,《夜深沉》的作者为项羽这位“失败的英雄”唱出一曲悲壮哀婉的颂歌。擅演大型历史题材的闵惠芬把这部风格浓郁的协奏曲演奏的尽善尽美,当年的“上海之春”也把创作奖和优秀演奏家颁发给作曲家和她。但她更加看重的是《夜深沉》在圆满完成作曲家的创作意图的同时,还为她在此曲中全力发挥“器乐声腔化”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间。她说:“《夜深沉》是‘声腔化’里程碑式的作品。”
从1980到1994,14年间闵惠芬首演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四部大型二胡的优秀新作。这是她为20世纪二胡艺术做出的一项伟大业绩,它是一项贡献,更是一种风范。在此前后,陆续有不少大型二胡作品问世,也有不少二胡演奏家参与首演,但公正地说,他们都是在以上各位作曲家创作和闵惠芬演奏的带动、引导和影响下相继接续的。风范是一个无形的榜样,中外音乐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由优秀表演艺术家引领出的新作、新风、新乐,在中国20世纪后半叶舞台上,闵惠芬的二胡艺术就是最杰出的风范之一。
三
闵惠芬对20世纪二胡艺术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她持续了四十余年的个重要贡献就是她持续了四十余年的对“器乐演奏声腔化”的追寻、探索和实践。作为首倡者,闵惠芬既有她本人极为多样广泛的试验,也写过专题论文进行阐释。同时,在二胡界,许多同行也给予积极回应并展开讨论和评述。
通过与她本人的当面交流,以及对以往二胡界论文的研读,我想提出的问题是:闵惠芬为什么花了几十年的演奏实践追逐这样一个演奏家的理想之梦?“声腔化”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艺术目的?对于20世纪二胡演奏艺术来说,“声腔化”实践会给这门艺术做出怎样的贡献?
要回答以上追问,离不开两个背景因素。一方面是历史文化的,其中包括:一、中国传统音乐数千年的成长历史中,声乐和器乐相互吸收、相偕进步,但在总体上,声乐的品种多,它对器乐的影响也大,很多曲目都是从声乐移植到器乐上演奏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二、中国古代人对音乐的表现能力的排列是“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认为人的歌唱在更直接地打动人心方面优于器乐;三、具体到二胡这件乐器,20世纪以前它是一件伴奏乐器,与各类声乐品种配合默契,天然地富有歌唱性。但自有了专业作曲家的新作以后,二胡那种天生的、具有传统歌唱性质感的特色似乎略微减弱。
另一方面则源自闵惠芬本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感性体认和她对二胡表现力的特殊追求。如前文所述,她自幼听到那些“乡下的声音”,无论她意识到与否,实际上对她日后音乐价值观的确立起到了一种“基底性”的作用。等到她选择了二胡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以后,以前的感性积累让她对戏曲、曲艺、民歌中“一吟即出”的地方特征和歌唱性有常人不,及的敏锐感。所以,当1960年全国二胡教材会议在上海召开,王乙老师带她向鲁日融老师学习《迷胡调》时,她立刻就生出了“穿人心肺”的强烈感受,并认为《迷胡调》是“把戏曲音乐化为二胡的音乐语言,把声腔艺术化为二胡韵味的创造性的成功的探索”③
闵惠芬在二胡演奏上自觉进行“声腔化”的试验始于1970年代中期。一开始,就碰到融多种声腔于一体,又蕴藏了不同行当、不同流派唱腔资源的京剧,将它作为“声腔化”探索的主要对象,实在是她的一次“知音”之遇。加上有京剧大家李慕良的直接指教,闵惠芬实现多年的理想就有了最好的保障。以她的演奏技艺和敏锐听觉,掌握起来当然很快。
但真正要连“流派”的韵味都能演奏到位,却必须对这种人类音乐文化中少见的“声音现象”有入木三分的把握。这方面,李慕良先生的真知灼见和数十年的操琴经验起到关键作用。比如,关于“言(菊朋)派”《卧龙吊孝》诸葛亮唱段,李先生指出:“言腔刚柔相济,剧中人物诸葛亮在这里一面表功,一面佯装假哭,声泪俱下,英雄‘动声色’而不动心肺,这种复杂的内心和外在表演要认真体会才可以通过演奏表现出来。”这里既有对流派声腔一针见血的判断,又有对具体角色心理的精彩分析,一语中的,让闵惠芬终生难忘。而更为深刻的是她“自省”式的感悟:“不仅仅是拉一个剧种,就是换一个流派,我都要求自己换一付骨头!”“要把这样的艺术内核表现出来,很费劲,但费劲也要学,‘费劲’说不定也会成就一种特色。”
“换一付骨头!”“成就一种特色!”这话,掷地有声,真诚感人。如果每一位演奏家乃至每一位专业音乐家在学习民间音乐时都抱着这样的谦卑态度,都能下“换骨头”的决心,我敢断言:中国当代音乐会是另外一个面貌。
那么,闵惠芬“声腔化”的最高目标是什么?质而言之,我觉得她是要让二胡更富于歌唱性,即要让手指下的“丝”与人的歌喉具有同等质地、同样美感的表现力。进一步说,她的目标,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歌唱性”,而是中国人的歌唱性。这种歌唱性的“根”在哪里?闵惠芬的答案是在中国各种地方戏、说唱、民歌里,为此她追寻了数十年。当我们欣赏了她演奏的京剧等十余种剧种唱段之后,再听她的《长城》、《新婚别》、《夜深沉》、《江河水》《二泉映月》,我们才能体味出她把“中国人的歌唱性”在自己的演奏中发挥到了怎样的韵致。
因为这一点,我突然想到,几个世纪以后,也许有人想知道20世纪后半叶二胡艺术家留下的音响,他首先选择的,一定是闵惠芬的演奏的《长城随想》、《江河水》 .. 因为,她是这个时代二胡艺术的杰出代表,她留给后世的,是真正的“时代琴音”!(本文图片由闵惠芬亲属提供)
①这个统计数字仅限于闵惠芬老师先后送给我本人以及在网上查检到的,肯定有疏漏。
②文中凡用双引号又未注明出处者,皆来自2011年3月17日本人与闵惠芬老师在江阴喜来登酒店的交谈整理稿。
③闵惠芬《西北吹来秦川的风》,1999年9月26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