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的最后几天,我与闵惠芬老师约好去她家聊聊,她在电话中便欣然答应。其实,在上海的近三十年中,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会议中,甚至在民族乐团和音乐学院里,我和闵老师的相见应算是非常多的,但真正能够坐下来深谈的机会,还真是不多,以至于常常让我觉得,和演奏艺术家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接触,更能够从音乐中寻找较为纯粹的客观话语。多年来,这几乎成为一个不似惯例却已经养成的个人习性。就要去见闵老师,一连几天,都在想着怎样和她聊,她会怎样讲?看着诸多的文献资料,其中三卷《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几乎记载了她所有的音乐故事和不同时期的艺术历程。这些研究中她自己写的“二胡艺术笔记”就有 27 篇,留下了许多可供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我时常翻阅并断断续续地读着这些感性而真实的文字,再听着她的二胡音乐,似乎和闵老师访谈的那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一年。事实上,距我们这次见面仅一个月后,闵老师就昏迷住院了。至今,远行的她已走了整整一年,而这一年竟好像从未在记忆中跳过。时间定格在我们面对面交谈的画面中,所有的思绪飘然而至。
闵老师的家舒适宽敞,她的嗓音很亮,脸上洋溢着和蔼亲切的笑容,和舞台上女神般的表情判若两人。想起她在舞台上呈现出的艺术形象,一把二胡、飘逸的衣裙、闵式的演奏风格及个人姿态,突然在如此真实的生活中相见,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还在紧张恍惚中的我,已经被她快速的问话拉回来: “怎么样啊?今天我们谈些什么呢?” “闵老师,您可以随意的说,都可以。”我赶紧说道。当然,我们彼此都知晓,二胡这个话题是中心内容。虽然关于闵老师的传奇故事,不论是艺术还是她生病时的种种经历我们都有所了解,但是,与她面对面的交流,确是非同一般。当你面对历经风雨沧桑的艺术大师时,敬畏之心会不由升起。抬头望着闵老师书房里那些安静地挂在橱柜里的二胡,它们是陪伴主人一生的知己,在它们发出的声音中,记载着闵惠芬二胡艺术世界时空转换的点滴瞬间。平常对她的理论、文献、音乐会、唱片、传说的研究都在近距离中放大。

一、民间艺术意味的缘分与生成
就像一个小姑娘那样,近七十岁的闵老师那可爱的表情和调高音调的嗓音,使你不会觉出她的年纪,更不会觉得她曾经得过大病。她开心的说: “其实,我常常觉得自己能够到今天,已经是赚回来了,没有理由不好好地继续我热爱的艺术!”八岁时,家乡的民歌小调、家中父亲的二胡演奏与她欢乐的童年生活相伴,而与民间音乐天然的缘分一直持续在她的一生中。她说起自己的“第一张剧照”, “那花裙子、那翘着的二郎腿,哈哈,好玩着呢”, “父亲教我的童谣叫小麻雀,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唱词是‘小麻雀,麻雀小,不会走路只会跳,不会唱歌只会叫’,音调全部记得。所以证明那个时候虽然小,但是音乐的感觉是准确的。(注释1)”她边说边唱起民谣来,描述自己当时悄悄听父亲拉琴时的神情,充满了儿童般的可爱与天真。或许正是这种天真再带些执着、接着地气唱歌奏乐,使得民间音乐在孩提时代注入的因子,在今后生活、事业的起落中,一往情深地陪伴着她。在民间音乐的初始学习中,大多是从喜好、从个人听觉感性出发,再从个人的感性体验中获得。对于民间音乐自然的接纳,与她生长的故乡那丰厚的民间文化大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古琴、昆曲、丝竹点点滴滴流入,家庭从小给予的民间音乐熏陶构成了和谐的纯真世界。

“记得初三的时候,拉刘天华的《病中吟》,阿炳的《二泉映月》都是附中高中的大哥哥大姐姐学习演奏,还轮不到我啊,那时候小啊。(注释2)”在学院学习,只知道像《空山鸟语》这样有技巧的乐曲,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练习的,民间与学院的关系是怎样的?对于年少的闵惠芬并非有清晰认识。但是,她是那样的幸运,在附中学习就遇到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大师卫仲乐先生、陆修棠先生、王乙先生、汪昱庭先生,他们对这个聪慧的女孩儿给予了专业学习成长路上的悉心指教。闵老师说:“汪昱庭先生了不起的,在当时,二胡新曲目较少,凡是社会上一旦有新曲,他就会带着我们去学,现在的老师也应该继承这样的传统。比方 1960 年,是全国二胡教材会议,来了许多各地二胡演奏家,汪昱庭先生就带我去看了从西安来的鲁日融,当他面对面演奏、讲解他编曲的《迷胡调》时,我当时十分兴奋,眼睛盯着看他的手法,耳朵听到不一样的音韵,那种新奇真是太惊喜了。(注释3)”对于听着江南民间音乐长大的闵惠芬,着实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民间音乐,这个时空像看万花筒一样,是如此的不一样,从孩提时听的、看的就在自己熟悉的生活里,而现在听到、看到的民间音乐是这么大的世界,喜欢的、熟悉的转换成要学习的一门艺术了。附中的学习对于一个学生基础奠定至关重要,进入专业学习阶段,在对民间艺术的认知上,她又遇到好的教育家,她动情的说“我们学习民间音乐,要学深学透学到家。” “这是 1958 年闵惠芬在附中开学典礼上,老校长金村田的讲话,从此这句话成为她从艺终身的座右铭(注释4)”,“这么多年过去了,在任何场合,我还是要说,这句话对我一生的重要”。
如果说在少年时期学习民间是一种天然的亲近,那么在经过附中、本科的学习后,她不仅在民族乐器的学习上,还对其他方面的民间艺术充满了好奇。她在许多场合中都提到:“在大学时代有幸跟江明惇、黄白两位民歌专家学了两年的民歌,对自己理解学习不同地方的民间音乐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民歌演唱的那些小腔儿常常在自己演奏中发挥作用。(注释5)”无论是当时的大环境还是学院的小环境,学习民间音乐的热情在他们这一代艺术家中,是奠定演奏艺术生涯的重要且美好的时期。那时,上海音乐学院在陆修棠担任主任时,先后邀请了“民间音乐家孙文明(二胡)、周治家(二人台·四胡)、张埃宾(二人台·笛子)、张小牛(苏南吹打)、婺剧音乐以及王秀卿(盲人艺术家,三弦、大鼓)、丁喜才(榆林小曲),在民乐系学习民间音乐蔚然成风,这对我们学习从事民族音乐专业打下了重要基础,是有深远效应的。(注释6)”闵惠芬对于民间艺术的喜爱也发生着变化,她不是孩提时期的以兴趣学习,而是广泛的学习和接纳其他地域的音乐、方言、润腔。比如他们去甘肃学“花儿”,去湖南学“花鼓戏”(当然不失时机的也看琴师的伴奏,看“花儿”、 “花鼓戏”的伴奏指法技法)(《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第一卷),其中有 27 篇闵惠芬老师自己写的二胡笔记。),“比如我拉广东的曲子,拉《寒鸦戏水》(郭鹰先生传授的),拉《昭君出塞》(模仿的红线女),像里面有很多不确定音高,是民族音乐中特殊的东西。当时他们艺人的民间的音律跟我现在不一样,所以会不习惯,你讲全像钢琴一样是绝对不好听的,全是半当中的,其实是写(记谱)不出来的。拉得好像喉咙发不出音,这样才有魅力。(注释7)”在叙述这段往昔时,她显露出无比的欣慰,这些学习的点点滴滴成为她日后艺术道路上最为重要的认知,也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她特有的“民间艺术意味”,这个观念与意义成就了她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层面上,支撑着强大的心理基础,行走在当代音乐的前沿地带。
二、民间艺术学习的续接与再度诠释
从1962年19岁那年开始真正学习演奏《二泉映月》,这首乐曲伴随闵惠芬一生,此后,这个学习几乎没有间断。儿童时代听父亲的演奏,好长很悲的这首曲子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附中高二那年,“学习《二泉映月》时,贺绿汀院长曾亲自给我上过一次课,在院长办公室。但是就这一次的课也是终身难忘。记得贺老说《二泉映月》不是描写风花雪月,他是阿炳用琴声来抒发他一生坎坷命运的一种愤懑的情绪,和对于光明的期盼。对这个乐曲如何理解,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启发。尽管话不是很多,但是这几句话引导了一生,更由于那么小就能够受到贺绿汀院长给我的期望,这种鼓励是一生的动力。(注释9)”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关心与指导,贺院长对闵慧芬与《二泉映月》给与了最初的旨意,不仅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热爱,更显现出一个作曲家对中国音乐的深深理解,贯穿于他自己的钢琴曲、歌曲、管弦乐曲等作品以及创作思想之中。这对年轻的闵惠芬来说,无疑是她深刻认知学习民间音乐艺术最为崇高的理性旨意。十年之后的1972年,冥冥中相遇,她从同学那儿神秘地得到杨荫浏、曹安和先生为阿炳录制的唯一的唱片,在上海电影乐团小小的昏暗房间中,拜录音中的阿炳声音为师,在守候着唱片学习的近半年多的时间里,阿炳的音乐世界多了一位如此执着的知音。作为再学习的民间音乐,二次创造的不断演绎,让闵惠芬更加认识到是民族器乐与民间艺术之间的亲缘关系,与其说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不如说这是二胡艺术中的一个重大的文化事项,在这个路径的探寻上,注入了传统音乐续接新生命的重大意义。从此,这首乐曲相伴二胡艺术,相伴闵惠芬的演艺生涯。
“这个学习的缘分,是闵老师的幸运,二胡这件乐器的幸运,阿炳的幸运,更是中国音乐的幸运。当年杨荫浏、曹安和先生的录音,将口传的、无声的民间音乐在极其特殊的场境中留存了声响,如果没有经过以闵慧芬这样的二胡大师们的再演绎,这首乐曲的声音存在方式很可能是另一种情形了!走出历史的情境,走出无锡的传播,走到更广泛的世界,年轻的闵慧芬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执着与热爱,造就了这首乐曲再现中国音乐舞台最初的生命力!(注释10)

如今,音准、音色、节拍、弓法这些技术在学院专业化学习下,有着系统的操练方法,有着青出于蓝的缤纷天地,但又有多少演奏家能够很好地把握阿炳的音乐自诉,而恰恰这是最难以控制和寓意的,虽然音乐总是被人们描绘成抽象的意义。闵惠芬从少时流淌在心灵的“民间艺术意味”,成为她再度诠释的解码,这种续接和持续在中国专业音乐学院培养的年轻演奏家中,的确成就了一个最为个性化的“闵惠芬现象”。
《江河水》虽然也是在附中高三的时候学习过,但是没有听过这首乐曲最初的东北双管演奏,对于其中的音腔并没有真正的理解。闵惠芬说:“实际上,我真正开始理解《江河水》是听谷新善吹的。当时是我在中国艺术团的时候,突然听说谷新善来了,马上去打听他的房号,见到他后我请他把江河水吹一下,他很高兴,大家面对面,他的双管由两个管子一样长,同时放在嘴里,两个哨子,音色非常的悲戚。吹奏后他给我做一些讲解,我们两个围绕着管子的‘涮音’和二胡的‘压揉’进行了探讨,虽说这个奏法是黄海怀先生的创造,但是怎样压揉,在音色、韵味上如何把握,很久没有找到感觉,听谷新善吹奏,清楚地感受到它不是我们二胡通常演奏的颤音,管子演奏音腔的幅度很大,频率特别快,棱角比较激烈”。《江河水》在双管吹奏的演绎中,管子悲戚的声音与人声有着相近似的声响,模仿哭泣的奏法,是管子独特的音色表现力。最早在辽南笙管乐中,最初的民间吹奏以人声的哭诉为观照,声音的构型清晰的透视出双管的特定情境。由二胡再次改编《江河水》后,闵惠芬的再度诠释,融进了二胡声音的特色,融入了自身个性的演奏特色。这个学习、思考、再创造的过程穿越不同的地域性、不同乐器的声音特点、不同情感的差异性表达方式,成为了二胡独奏艺术的经典作品。向双管吹奏的学习,为二胡艺术的表现,有效的寻找到与民间艺术接壤的途径,这是一种续接、补充、延伸,闵惠芬对民间艺术所持有的认真态度,成为《江河水》情感表现的某种象征意义。可是,这是多么大的挑战,每每在舞台上演奏,她都要有着极其饱满的情感进入境界,使乐曲的寓意在不同的时空转换中,释放出强大的情感宣泄。
我问她:“《二泉映月》《江河水》从你年轻时拉到现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她感慨的说:“几十年来坚持演奏《二泉映月》《江河水》,这两首曲子拉了大半人生,至今觉得还是没有拉好,觉得太难了!”这两首作品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唱片中不知演奏多少回,但每一次,闵惠芬先生的演奏都是那么的认真投入,把民间的曲调一次次变成“充满情感的艺术作品”。闵老师说:“作为演奏家,很多音乐是当时、当地,在那个环境中,不是每遍都一样,但是,每遍都有它的时期的特殊性。(注释11)”我想说,这两部源于民间音乐家、民间艺术的曲调,在闵惠芬的二胡艺术中,为中国的二胡“作品”做出了卓越的再创造。“‘音乐作品’这个概念还包含着一种东西,那就是作品的整体完整性。对这种完整性决定作用的是各个阶段结构的性质。达到这种完整性的方法在历史上是变化着的,在不同体裁的音乐中都不同。在其间的蓬发着、奔涌着热情和诗意。(注释12)”在这热情和诗意下,反复的琢磨、声音呈现,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化作“闵式”的特有符号,她的个人性格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中,将特定乐曲的声音纳入,把民间音乐特有的概念、语汇最大限度的挖掘出来。
三、音乐艺术观念的叙事与轮回
20世纪70年代闵惠芬提出了“器乐演奏声腔化”的观念,这是作为一位二胡演奏家在理论上的新想法、新思路。我们知道,许多演奏家在表演与实践上有着辉煌道路,但是与艺术表演理论的研究存在相对的距离。闵惠芬对于“声腔化”这个主题概念的思索,事实上是她多年以来的内在体验:还在中学时,她已演奏了京剧曲牌《八叉》,使她一直对京剧音乐有着特别的喜爱,同时对器乐语言与声腔语言、二胡与人声中特有的声音润腔、特有的表现特色着迷,她一直在寻绎着这两种艺术之间的相通与相合,试图在器乐化语汇原有的语言表达上,借鉴戏曲声腔的润味,加大二胡声腔的表现力。这个概念的提出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文化传承,并非偶然,是自然自觉意识下孕育出来的,是闵惠芬艺术观的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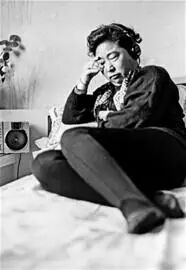
连波先生曾写到:“闵惠芬仿奏的京剧唱腔,除了《卧龙吊孝》,还有别的流派唱腔,如高亢激越高(庆奎)派等,这对他开拓多样的演奏风格很有好处。比如后来她仿奏的越剧《宝玉哭灵》、黄梅戏《打猪草》、粤剧《昭君出塞》以及迷胡调、二人台等南北不同风格的音乐都能够很好地表现出来。(注释13)”听这些戏、学习这些声腔,成为丰富她器乐表演的另一个场域,在这里二胡音乐的体裁、题材、演奏等成为她鲜明的审美取向,并包容了更多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事项。因此,“声腔化”的艺术理念使她的演奏实践更为纯粹,尤其在演奏了诸多与情感象征意义相关联的乐曲之上,她对悲喜传情、音韵旨意的认知有着更为理性的思绪。在民间,中国人的听觉惯常“喜形于腔、悲诉于腔”,没了腔的调儿、没了腔的曲儿,音的意义、声的意义,缺失了最赋予生命力的情感表现,这与闵惠芬的二胡艺术始终贯穿的音乐思想是是一致的,是吻合的。“器乐演奏声腔化”基于表演实践,对民族器乐尤其是拉弦乐器的表现性上有着普遍意义,从语义上、声调上强化了弓弦乐特有的内在特征。这也是闵惠芬在后期二胡艺术中,大多选用不同戏曲声腔剧种的经典段落,学习、移植、改编成二胡独奏曲的原因,这些音响的相关特性,渲染和加深了二胡音腔的表现力。歌唱的内心与手指操琴的相合,在她诸多二胡独奏曲的表演中,在左手滑揉、右手运弓上集结着如诉如泣的音腔运动,情感表达自然、自如、自在。
她感慨的说:“有一半人拉琴,我称之为‘操作(音乐)符号’,我是最反对的。他的动作只是在那里动一下。如果那些动作也好,音乐的线条感也好,真是自己的音乐境界发自内心的才好,这是我一直强调,也跟我的学生们反复说。我说你们动作都对,就是不动人。(注释14)”内心的动感和外在的动感,对于情感的表达意义也有着不同时代的理解,老派演奏家与新派演奏家不同审美观念下有着个体的心理取向,但是在传统音乐文化的建构上,确是值得深思的。在当代中国音乐中的确存在困惑,于今日,这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重意向、重传神这些特有的中国美学资质,被弱化在技术操练的表现主义活力中;器乐化的技术又是在当代大多数艺术、大众群体注重的方式。这在文化意义上就有一定的难度。在学院内、学院外,专业与民间,两条线路在闵惠芬老师那儿,民间艺术却像是一个滋养乐心的乐园。
比如,凡是外地来请教闵惠芬二胡的民间艺术家,几乎都有着一个不成规矩的“规矩”,那就是必须向闵老师留下当地的民间音乐,一首民歌、一个唱段、一二句方言。为戏曲伴奏的胡琴,那些充满多重意义的声腔,都是闵惠芬学习的兴致,参照的符号,在声腔、音腔互补搭配,合理共存。京剧《逍遥津》《卧龙吊孝》《斩黄袍》,越剧《宝玉哭灵》、黄梅戏《打猪草》、粤剧《昭君出塞》等,哪些不是由声腔发出的二胡艺术?不论是还原还是再现、亦或是再创,旧有传统的再生还是新传统的新生,都足以窥见声腔艺术对这件乐器的深厚影响。民间音乐是她立足之地的根,在专业化的环境中得到升华,在大半生的艺术理念上养育了精神和灵魂,并以此填补了专业化教育的不足,凭借这份质朴的心,执着走自己的路,发出自己的声音。
不论“民间二胡”“文人二胡”,还是“学院二胡”“专业二胡”,较之于其他中国民族乐器,二胡率先在专业、非专业、职业与非职业、学院与民间中走出属于自身的表演途径,也形成了二胡艺术特有的“音乐文化模式”。相比较其他乐器的生存现象,是相当突出的。更由于随着二胡业界几位大家特有身份的出现,他们几乎都是集创作、表演、学院、民间为一身的二胡艺术家,众所周知那些炙脍人口的二胡曲,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宏大命题下,置身于民间的土壤发酵:有刘天华这样的大师融中西一体,带来了百年二胡的发展态势,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或浮出水面、或激流涌动,留下浓重的被续接的痕迹,在历史中过往;有阿炳这样的大师,在江南民间音乐的的土壤里自由生长,历经半个世纪里恢宏壮观,听得见不息的回声,或被改编成协奏、或与交响相合、人人感慨这是最原始的中国音乐的表达方式;有孙文明这样的大师,他留给后人那技巧繁华、内容丰厚的10首二胡作品,足以震撼二胡炫技的斑斓世界,不论是非乐音、手指弹弦,还是箫声、八度定弦,恢宏壮观,如潺潺流水为后人惊叹;更有闵惠芬这新时代的艺术大家,将那些植根于泥土芳香的传统经典,架构了一片看得见、摸得着的彩虹。“有人说闵惠芬的《二泉映月》《江河水》《长城随想》是她艺术生涯的三部曲。这三首乐曲不仅是她艺术水平的代表,也是她人格魅力的写照。作为一位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培养出来的最具代表性演奏家之一,无论在学院还是大众,对二胡音乐的认识、对闵慧芬先生的这三部乐曲的熟悉,已经转换成‘二胡音乐的特定语汇’。(注释15)”当这些中国音乐中的经典走进每一个人时,闵老师以及他的同行前辈们所努力传承的历史事实,所画出的民间艺术那宽厚、朴实的大地,带给后人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命题。她动情的回忆:“当年父亲去看望杨荫浏先生时,他的问话几乎成为我一生的激励。杨先生说,阿炳的肚子里有千百首民歌、戏曲,你有吗?我顿时觉得汗都给他问出来!但是这种震撼是一世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一直这么努力地学习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和这都有关系。(注释16)”这是一种精神,是成就闵惠芬二胡艺术的基点,与民间艺术相生,与民间艺术相遇,叙事着她艺术生命的轮回。
结 语
有很多东西注定要成为记忆的,或者封存、或者遗忘、或者散落、或者淡忘、或者还会被误解,这是历史的宿命。在被评说和被理解的过程中有着形形色色的解说,有意味的是,那些留存的音乐,那些音乐中的情感阐释,历久弥新。“闵式”演奏艺术的指向性清晰了然,在民间与专业化行进的双向路径中,她无疑是被历史铭记的。由此,不禁使人联想,民间音乐中最富有记忆的就是世代传承的东西,而专业音乐最善于的是用技术、用创新去解读。二胡艺术在今天的发展,几乎成为了中国民族器乐艺术发展最快的专业。从闵老师第一代专业院校培养出的二胡艺术家,到今天一代代年轻的二胡演奏家,新的作品越来越多、新的技法越来越丰富,舞台的华丽、服饰的时尚、乐队的庞大、弓法与指法不断的超越。当我们比对当下,回望传统时,从胡琴到二胡、从民间到学院,在传统音乐与当代音乐对接与交错中,闵惠芬以她个人的姿态走在人们的视线中,走在这个时代的前沿地段里。
今天,我们很难用一个什么定义或一个合适的比喻来形容她、概括她,即使有这样那样的评判,都显得过于概念化、符号化。事实上,在许多关于她的研究中,都有着这样的倾向,而对她艺术生涯形成的途径及其对二胡艺术当代历史格局的影响,则需要更深度思考,这也是中国民族器乐文化在当代艺术化、专业化教育体制下值得思考和反思的。在半个世纪的演奏艺术历程中,几经风雨彩虹,迈过坎坷与病痛的磨难,她却始终在艺术的舞台上展示个人独特的魅力,在社会变革中以艺术的表达阐释自身。她的存在不仅是中国当代二胡艺术的代表,是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民族乐团的骄傲,更是解读中国民间艺术、当代二胡艺术作品在二度创造、传承实践、表演探索的真实范例。巴金说过“我愿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闵惠芬的二胡琴音,在中国浩瀚的琴声中,化作“大地茫茫,河水流淌”,将《二泉映月》《江河水》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听觉中。不知是谁说过:记住一个人,也就记住了一个时代!手机里还存着闵老师2014年春节大年初一发来的短信:“唱一首二人台名曲以示节日祝贺。过罢大年头一天,我和我的树荟老师来拜年,一进门,把腰弯,左手挽来右手牵,呀子依儿呀呵,师生相交拜的是什么年依呀呵。闵惠芬”。而今,她已远行,她是一个精神上的勇士,她极具感染力的二胡艺术总是在人们心中回响。回顾、思考、传承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可忘却的纪念。
注释:
1.闵惠芬口述。
2.闵惠芬口述。
3.闵惠芬口述。
4.方立平:《闵惠芬二胡艺术与她的“大中华心结”》,傅建生、方立平(主编):《闵慧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5.2004年9月,在“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器乐教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6.《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之“忆恩师陆修棠先生”,第26页。
7.《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第一卷),其中有27篇闵惠芬老师自己写的二胡笔记。
8.闵惠芬口述。
9.闵惠芬口述。
10.郭树荟:《规约 感知 想象——以陆春龄、闵慧芬二度创作的审美取向为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23页。
11.闵惠芬口述。
12.卓菲亚 丽莎,于润洋(译):《音乐美学新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 年版,第16页。
13.傅建生、方立平(主编):《闵慧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第244页
14.闵惠芬口述。
15.郭树荟:《规约 感知 想象——以陆春龄、闵慧芬二度创作的审美取向为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23页。
16.闵惠芬口述。
作者简介
郭树荟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导、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教研室主任、中国民族管弦乐理论评论委员会副主任。上海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理事、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中国传统音乐、20世纪中国民族器乐、当代社会语境中的中国传统音乐,中国音乐美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