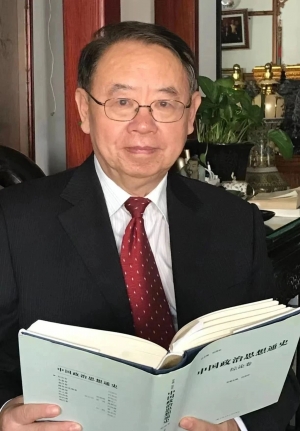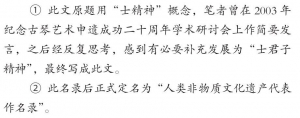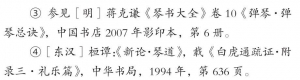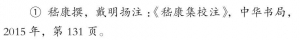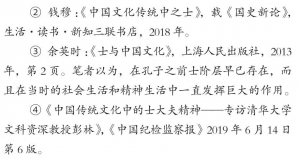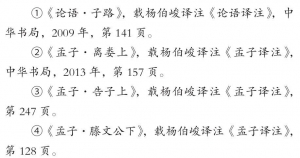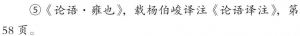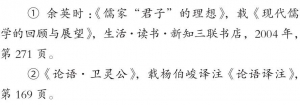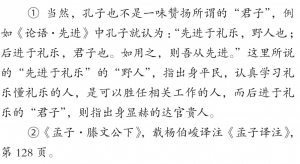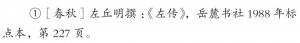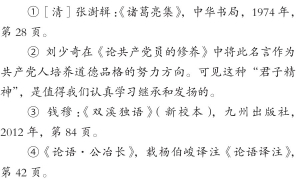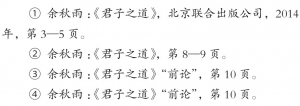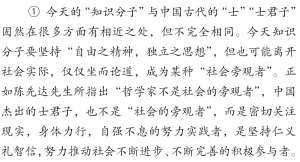秦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摘要】古琴作为中国古代士阶层特有的乐器,是士君子精神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孔子终身弹琴不辍,并以“乐教”为核心,其教学目标正是努力培养完美的士君子。历史悠久、积累丰厚的中国琴乐艺术及相关文化传统是宝贵的中华文化遗产,士君子精神则是“琴道”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古琴文化精神中不可忽视的核心要义,我们应认真传承并弘扬这一优秀文化传统。
【关键词】古琴文化;琴道;士君子精神
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申遗成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第二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②,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自此也开启了其天翻地覆般的成长壮大新历程。
但回顾古琴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古琴进校园以及申遗成功后的新发展,可说一则是喜,一则也忧——喜如上述,忧则是感到在古琴文化传统的传承发扬方面,还明显存在某些不足。古琴在“艺术”方面,比如“纯音乐”方面(如古琴音乐创作、表演、传播等方面)获得重大发展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对传统古琴文化及相关文化精神的认知、传承和弘扬方面,多少有些滞后、薄弱。古琴艺术,首先是古老而辉煌的传统音乐艺术,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极富特色、历史极其悠久、积累无比丰厚的突出代表。其独特鲜明的文化特色和精深宏大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巨大的精神财富。对此,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一
有关古琴艺术的文化成就与精神特色,自古以来便有各种各样的归纳总结。中国古代就有“神龙作琴”“舜弹五弦琴而天下治”等传说,认为琴是远古“圣人”所发明创制的、治理天下的重要工具。传说经过周文王、周武王各加一弦(也有传说“尧加二弦”),才使得琴成为“七弦琴”,并以宫商等弦代表君臣之位。古人认为古琴具有“明道德”“感鬼神”“美风俗”“妙心察”“制声调”“流文雅”“善传授”等“七利”③,还提出“琴者禁也”的说法,认为琴乐能够“禁止淫邪,正人心也”④,表明人们对古琴的艺术、文化功能有非常广泛的理解和高度的认知。古人还认为琴是“德”的集中体现,认为在八音之中,“琴德最优”,所谓“愔愔琴德,不可测也”①。因而,琴被认为是八音之领袖、八音之总统。“万世师表”的孔子,是先秦最伟大的琴家和琴乐文化的大力推广传播者,他认为“道”是宇宙人生最高的哲理,是指引人们走向光明的坦途大道,曾发出过“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誓言。汉代的桓谭,已明确提出“琴道”概念——当时人们对琴乐和琴文化的评价,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崇高境地。人们历来认为琴是文人雅士专属,所谓“君子常御”的“最亲密”的伴侣,是“修身理性,反(返)其天真”的最高雅之艺术。宋代朱熹更是把琴视为探索宇宙和世界奥秘的最好精神伴侣,他在《紫阳琴铭》写道:“养尔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子钩其深。”后来,人们更是认为明末清初以虞山琴派为代表的“清、微、淡、远”的意境,是琴乐艺术和文化精神的最高美学追求,也是琴乐从乐曲创作到演奏的精神要义。总之,古人认为琴为远古“圣人”所制,象征天人合一,体现阴阳五行,具有种种神奇功能和崇高道德,是实现礼乐治道的重要工具,也是“君子”自我控制的工具。所以,被视为八音领袖的古琴艺术文化,体现了无比精妙的中华艺术精华,也代表着无比崇高的文化思想价值。去除古琴头戴的华丽王冠,以及种种神秘附会的锦绣外衣,中国传统的古琴文化的精神要义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古琴文化最核心的精神要义是先秦以来形成并长期被坚持和发扬的“士君子”精神。
二
“士”原是古代中国的特殊社会阶层,后来则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突出的社会文化群体——士大夫群体、文人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 号称“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人群,主导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主流文化和主流思想,是中华文化“大传统”的创造者和主要传承者,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士阶层(或士群体)的存在及其长期处于社会中心位置,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钱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指出:“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②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的引言——《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中也说,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遗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③。中国与古印度、古希腊,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世界的三大古典文明中心。清华大学彭林也指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是以人作为中心,是将人如何通过修身进德成长为君子,如何从动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为道德理性意义上的完人,作为社会发展最核心、最基础的命题,这是中国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士大夫群体之花盛开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根本原因就在这里。”④那么,士阶层以及士群体本身有哪些特点?
(一)早期的士是文士,也是武士,是文武全面发展的低等级贵族
先秦的“士”,原是次于天子、诸侯、大夫的低等级贵族。他们从小就必须认真学习和传播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等多种传统知识。所以,早期的士是文武双全、全面发展的;更重要的是,士不仅要经受良好的、全面的教育,还要努力培养优秀的思想品质。
士平时担任下层行政官员,或充任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天子、诸侯的宫廷和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一般职事官;战时,则执干戈保卫社稷。当时,只有士才有资格随身佩剑。西周直到春秋早期,只有士才能够充当战士上前线打仗,老百姓即所谓的“野人”、奴隶、刑徒等,上阵打仗时只能做后勤或服务性工作。所以,才有“士兵”“战士”等称谓,至今还在运用。
(二)“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以天下为己任、死而后已的远大志向
先秦文献中,对士的思想精神、气质人格有许多阐述。孔子提出了“士”的理论标准,《论语·子路》(以下引用《论语》或只举篇名)中,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就是说,只有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才能称为“士”。《泰伯》中曾子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认为“士”必须要有宽广、坚韧的品质,因为认识到自己责任重大,道路遥远,要有勇往直前、“死而后已”的精神。《里仁》中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意思是立志于追求真理的士,如果还以穿破衣、吃粗糙饭食为耻,这种人就不值得和他谈论真理了。这是孔子对士应有态度的一种告诫和期望。
(三)士应具备其他种种美德
《论语·子路》载: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在孔子看来,“行己有耻”“不辱君命”方可算得上“士”,差一点的,像怀有孝悌之心,有着良好口碑者的,也可以算得上士;再退而求其次,那些做人诚信、行动果断的人也还凑合;不过当时的统治者(“今之从政者”)却算不上。从孔子的话里,我们也听出多少有点儿“肉食者鄙”的味道。
士的美德还有很多,例如子路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也。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①《宪问》:“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居,本义为居处,此处引申为舒适,安逸。《子张》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见危致命,遇见危险时要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
进一步讲,《论语》说士要“志于道”,“道”,不仅是道路,通道,还有道理、道德、道义等含义,在孔子看来,“道”就是宇宙人生最高的哲理,是指引人们走向光明的坦途大道。所以孔子甚至表示自己“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所言士要“行己有耻”,也就是说士对自己的行为要有羞耻之心,上要维护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失,下要维护个人的尊严不受伤害。在此基础上不辱君命,才称得上是上士。
孟子则说士“尚志”,是说士首先要立志,这个志,就是“居仁由义”,而做到这一点,“大人之事备矣”,就是君子了。所以他反复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②“仁,人心也。义,人路也。”③居仁由义,就是以仁存心,依义而行。他还提出了士品格的高标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④
三
依据孔子观点,按照从高到低的标准,士被划分为上士、中士和下士三个不同的层次。老子《道德经·第四十》有“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的说法,也将“士”区分为上、中、下不同层级。
先秦之“士”又称“君子”,有时也连称“士君子”。有学者指出,在先秦文献中,“士”“仁者”“大人”“大丈夫”以及“圣人”等观念,也都是和“君子”相通的。但若进一步细分,“士”与“君子”有所不同,“士”强调的是社会等级身份,而“君子”则更强调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的修为。《论语》中有关君子的讨论,显然偏重在道德品质方面。
孔子曾明确指出,有“君子儒”,同时也还有“小人儒”⑤;故所谓的“君子”,指的是士(以及后来的儒者)中的优秀部分,就是上士。由此可见,“君子”并不等于一般的“儒生”“儒士”,必须是高等级高修为的优秀儒生、士,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更优秀的士,才称得上是“君子”。
“君子”有着不同常人的宗教般的救世情怀,这种救世情怀,孔子称为“仁”:他们要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天下苍生,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正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因此,余英时明确指出:“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有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的观念,……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①
由此可见,“万世师表”孔子所开创“孔子学院”,其教育方针,是以培养其心目中的“士”“君子”为目标的。孔子的教育方针是“立人”,不仅要“立于礼”,更要树立远大志向,成为不可不弘毅的、具有高尚品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高等级的“士”,即“君子”。也正是由孔子始,君子才正式成为一种道德的理想。
如果说,我们今天教育强调培养“四有新人”,孔子则强调所要培养的君子,必须能够在其“四教”(文、行、忠、信)中成绩合格,具备并能够实践 “仁、义、礼、智、信”的能力和志向!孔子提出“仁”的概念作为礼乐的核心精神,仁的实践方式就是“礼”,所谓“君子以义为质,礼以行之”②,强调“仁”与“礼”二者在君子的实践中决不能分开,所以“君子”的本质就是“仁”。在孔子的谈论中,“君子”往往与“小人”对比,从而体现出君子的种种优秀见识与品德。如《论语·述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说“君子”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小人”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而不比”则与“群而不党”相互比对;又如《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左传》以“立德、立功、立言” 为三不朽,孔子这里提出了“怀德”的观念,认为自觉的道德是人生立身之本。
《大学》进一步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儒家的这个德,同样受制约于礼,礼更高于德。
“君子”与“小人”的比对区分,《论语》中比比皆是。比如: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子罕》) ……
《论语》所讨论的核心也紧密围绕士君子精神、品格如何培养。如: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提出了“君子”的理想人格目标以及“修己安人、安百姓”等具体要求。孟子自称“所愿学孔子”,进一步对君子人格,特别是对士的人格,做了系统深刻的论述。①
《孟子》鼓吹士君子要具有“浩然之气”。他说: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还对士精神有多方面且进一步的揭示。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②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品格,也是士不可不弘毅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浩然之气”的展示。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而做到志不可夺,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基础就在养浩然之气,就必须具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孟子还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孟子又说:“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
孟子相关论述成为后世士人修身的准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养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士君子被认为是古代文化精神的优秀代表。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关于士、君子的标准,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纸面上的说法,其中固然有某些理想的、溢美的成分,但总体而言,是来源于实践的,是从当时士君子“仁义礼智信”方面大量真实、生动的行为事例中总结出来的,是有充分的现实依据的。如赵国的蔺相如就是士君子的生动例证。他在秦强赵弱的形势下,在外交活动中,能够舍生忘死,勇敢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完璧归赵”的故事,渑池之会迫使秦王击缶的故事,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而当武将廉颇不服,认为蔺相如无非凭三寸不烂之舌,便成为上卿,因而到处找碴时,蔺相如却示弱,努力避免与廉颇争名夺利。蔺相如顾全大局的考虑被廉颇发现后,廉颇羞愧难当,主动袒露上身,上 门“负荆请罪”。可见作为武士(武将)的廉颇,也具备君子“坦荡荡”之品格。这些士君子的举止,都令后人赞赏不已。
又如,《庄子》所载“信若尾生”的故事:
尾生与女子期于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
战国时期鲁国的士人“尾生”,与女子约定桥下相会,女子未如期出现,河水不断上涨,但尾生仍坚守约定,抱着桥柱直至被水淹死,毫不动摇!这个以生命为代价的约定,体现了士极高的守信和忠诚。故事中的尾生一直被人们高度赞誉,是当时人们向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风尚的有力注脚。
四
从历史上看,特别是从西周以来长期沿袭的礼乐文化的相关等级制度中,古琴(还有瑟)最早是“士”阶层的代表性乐器。一方面,在以“金石之乐”即钟磬乐为最高礼乐等级的先秦,天子、诸侯等享有“宫悬”“轩悬”“判悬”,士等级也可以配置钟磬,但只能享有“特悬”(即“特钟”“特磬”,是单件钟、磬),其等级礼仪功能显然大过实际演奏音乐的功能。另一方面,《礼记·曲礼下》有“士无故不撤琴瑟”等明确规定,说明琴瑟之乐是士阶层真正代表性的乐器和音乐。
士阶层也好,士君子也好,与音乐、古琴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先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甚至罕见的、真真正正的“爱乐时代”!
当时的音乐,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乐之邦,所以孔子和儒家极其强调礼乐文化的重要性。礼、乐并举,“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二者缺一不可,是实现天下大治必不可少的根本举措。所以,历朝历代,包括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强调“王者功成作乐”,以表明自己政权的正统合法。
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则认为“礼者为异,乐者为同”,所以“乐”在凝聚人心、教化民众方面极其重要,其作用不可替代。由此,儒家公开强调“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认为“乐”具有改变社会成员行为举止,调整规范人们行为方式的力量。
孔子认为,士君子的教育培养过程,亦即“立人”的步骤,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说自己年十五而志于学,但也要“三十而立”,即到三十岁才能实现“立于礼”;而人生最后最高阶段的追求,则是“成于乐”!可见“乐”是人生不断努力的最高成果,是教育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由此才能成为士、君子,才能够“游于艺”,实现最大的自由,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如前述,琴相传是远古圣人创制,“舜弹五弦琴而天下治”,后经周文王、武王各加一弦,才成为七弦。七弦还象征着君臣关系,固大力提倡士君子精神的孔子更是身体力行,带领弟子们努力学习“诗乐”和琴瑟之乐。有关孔子与音乐尤其是古琴的关系,有大量生动事例。例如,孔子终生不离琴瑟,《史记·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墨子批评儒家的“乐教”,讽刺他们成天“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没有时间治国理政。
孔子还谆谆教导儿子要认真学习诗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西周以来贵族的社会生活中,“赋诗”是培养士的必修课程,可见音乐的交流沟通作用,甚至比言语还重要。
孔子认真学习和感受音乐,有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传说。孔子认真向师襄学习演奏古琴曲,反复刻苦练习,不仅力求“知其数”,还要“知其志”,直到后来“知其人”,即感受到乐曲所刻画的文王,才达到目的。后来师襄才告知,该曲正是《文王操》!
孔子带领弟子们四处游学,哪怕被困在陈蔡,受冻挨饿,仍专心致志弹琴不辍。而且,孔子还作有琴曲《陬操》
。孔子和他的门徒热爱琴乐的事实,兹不一一列举。总之,孔子及其门徒努力实践着“士无故不撤琴瑟”的礼乐规定。可再举一个生动的史例,足证“士无故不撤琴瑟”绝非虚言。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
冬,楚子伐郑以救齐,门于东门,次于棘泽。诸侯还救郑。晋侯使张骼、辅跞致楚师,求御于郑。郑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国之人,不可与也。”对曰:“无有众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娄无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后食之。使御广车而行,己皆乘乘车。将及楚师,而后从之乘,皆踞转而鼓琴。近,不告而驰之。皆取胄于櫜而胄,入垒,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挟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复踞转而鼓琴,曰:“公孙!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谋?”对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则怯也。”皆笑,曰:“公孙之亟也”。①
这则文献讲述当年冬天,晋国、郑国联合抗击楚国大军。晋、郑三位勇士,由郑国勇士射犬驾驭战车前往突袭、挑战楚军大营,这是何等英勇果敢的行为!如此紧张、严峻、危险的进击时刻,两位晋国勇士居然“踞转而鼓琴”,即蹲在战车上弹琴(由此推测,当时琴可能像曾侯乙墓出土的琴那样,远不如今琴长)!等战车冲进楚军大营后,他们赶忙放下琴,拿起甲胄、武器,与众多敌军搏斗。后因敌众我寡,不得不跳上车撤退,并抽弓射箭御敌。一旦脱离敌营后,两勇士继续“复踞转而鼓琴”,无比豪迈。
这一生动事例揭示了先秦士与琴之间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充分说明“士无故不撤琴瑟”!当时之士(武士)舍生忘死、勇往直前、不可不弘毅的精神,也由此跃然而出。
要知道,这还是发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联想这时一心要复兴“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礼乐盛况的孔子及弟子们,对琴乐无比推崇,我们完全可以合理推想:西周时期士与琴的关系,是何等亲密无间!琴乐在当时士阶层中也必然极其盛行!
大家熟知伯牙、子期“知音”故事:伯牙弹琴,得遇知音子期,指出他所奏琴曲“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后子期夭逝,伯牙为之终生不复鼓琴!其实,这也是当时所推崇的“士为知己者生”精神的生动体现。
正因为先秦的士、士君子文武兼备,心存浩然之气,“不可不弘毅”,能够舍生取义,可知当时琴乐的精神风貌、音乐品格,绝不是后人所说那样一味的“清微淡远”,所以才会有《聂政刺韩王》(即后来的《广陵散》)等琴曲(武曲)作品产生。汉代,琴更被推崇为八音之首,八音之统,在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琴乐及其文化精神,更被桓谭推崇为“琴道”,达到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
五
士君子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史上“正气歌”所讴歌激励的精神。《论语》说士要“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不可不弘毅”,要舍生取义。孟子则说“尚志”,也是说士首先要立志。士君子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在中国古代优秀的文人士大夫中,秉承这种精神气概的人物层出不穷,士君子精神也不断得到阐释补充、发扬光大。
诸葛亮晚年撰写的《诫子书》,开头就指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①可见,诸葛亮是以“君子”作为子女思想、行为的方向和标准的。
宋代范仲淹在著名的《岳阳楼记》中写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士君子救世情怀最通俗、最精辟的注解。而这里所说的天下,已不局限于一家一姓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名言。②宋代的张载,提出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士君子精神的升华,体现了士君子的最高人生理想。尽管很难实现,但所体现的思想内核和心灵追求,却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人文精神遗产之一。宋末文天祥抗元失败,被俘囚于土牢,曾作《正气歌》,引先贤事迹,颂浩然之气,激励自己,说“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文天祥《正气歌》上承先贤,又启示后人,“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成为士人以及所有有志之士的追求和重要的精神支柱。晚清的左宗棠被梁启超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他捍卫国家主权,先是大力加强“海防”,后致力于“塞防”;在国势日蹙江河日下的时代,曾在60多岁时借款、抬棺出征,收复伊犁,被列为晚清十大民族英雄之首!他的一生,不仅充分体现了爱国爱民的伟大精神,也生动体现了“士为知己者生”的光辉文化精神。早在左宗棠37岁还是举人出身的乡下教书先生时,便被著名的民族英雄、刚从云贵总督高位病退的林则徐看中,将收复新疆的历史重任以及自己历年搜集的相关历史、地理资料等托付于他!他不负林则徐重托,不怕千辛万苦,高龄抬棺出征,收复了中国近六分之一的领土,写下了令人赞叹的士君子“魂魄之光”!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一部四千年中国史,正是一部浩气长存,正气磅礴的中国史,不断有正气人物、正气故事。故使中国屡仆屡起,屹然常在。”③士君子精神,则是“一部浩气长存,正气磅礴的中国史”中不可轻视忽略的民族精神中的高光亮点,是中华文化精神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灵魂的光辉展现。
孔子主张士“从道不从君(君王)”,“君”也得服从于“道”,因此,孔子还主张“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他说如果“道不行”,自己将“乘桴浮于海”④,即自己追求的“道”如果实现不了,宁肯坐小筏子出海,离开这个地方。这体现了士君子坚持和保留自己独立思想与精神原则,以及个人尊严与独立人格的决心。
孟子还主张士即便在君王、权势者前,也要坚持独立人格和尊严。即便没有条件,无法实现士君子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孟子主张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是一个优秀的士君子必须坚持的生存原则和处世底线。孟子对历史上民众推翻暴君、发动革命改朝换代的事例充分加以肯定。因此,孟子及其著作受到了后代集权专制的帝王们的否定、排斥,甚至阉割。
一方面,自古以来的有识之士不断努力继承弘扬先秦士君子精神,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秦汉以来在专制集权统治下,推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开办科举,让士君子以及读书人的独立人格逐渐丧失,士君子精神不断消减、失落,甚至发生变质。先秦文武兼备、心存浩然之气、“不可不弘毅”、能够舍生取义的士和士君子,绝不是后来那些只读圣贤书、一心求取功名利禄的文人士大夫形象,更不是后来戏曲中文弱小生所展示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形象。然而,随着文武双全的士君子的独立社会地位的下降、人格精神的没落,以及士群体在社会结构中逐渐“边缘化”(余英时语),古琴所依托的士君子文化精神也不断消减。在清代统治者所鼓励的“清微淡远”等世风时尚影响下,琴乐刚健勇武、积极进取的一面,也不免逐渐消减。
结语
综上,中国传统的“士君子”精神,主要有“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以天下为己任、死而后已的远大志向。孔子还说“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关于君子,则还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和品德。孟子强调:“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尤其与“小人”对比,则更凸显君子(亦即大丈夫)的各种优良秉性,包括仁义礼智信等崇高品格和荣誉感。
余秋雨先生在《君子之道》一书中强调,“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人格(personality)”,“中华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所以要“复兴中华文化,也就是寻找和优化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他还说,“对于一般人来说,文化的最后一级台阶,就是为灵魂找到故乡,或者说,找到有故乡的灵魂”。①
那么,“中华文化的集体人格模式”是什么呢?余先生明确指出:
与“圣徒”和“绅士”不同,中华文化的集体人格模式,是君子。
中国文化的人格模式还有不少,其中衍伸最广、重叠最多、渗透最密的,莫过于君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庞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最大公约数”。
“君子”,终于成立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识。②
他还说“君子”两字包罗万象,非同小可,“儒家学说的最简洁的概括,即可称之为‘君子之道’。甚至,中国文化的钥匙也在那里”③。因此,他强调“对中国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么都有了;没有君子,什么都徒劳”,所以,“儒家对中国文化作了理想性的回答:做个君子”,而“做个君子,也就是做个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国人”。
余先生下面一段话,也是发聋振聩的:
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溃。中国文化的延续,是君子人格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刚健,是君子人格的刚健;中国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国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④
由此可见,君子精神在中华文化传统和思想精神文化传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我们文化的故乡,灵魂的故乡,也是我们文化故乡的灵魂。
琴既然是士阶层士君子的专有乐器,先秦的琴乐(乃至后世琴乐)也就打上了士君子文化精神的深刻烙印。后世的文人、士大夫虽然也有不少人努力保持弹琴的传统,但“士无故不撤琴瑟”的传统与士君子的优良传统,包括儒家“君子”理性的三要素“知、仁、勇三大德”也并未被后世文人士大夫完好继承。
春秋时期士君子文化,得到比较自由的创造活动空间,出现了群星丽天的诸子百家学说,构成中国思想文化的“轴心时代”,深远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进程。士君子精神也长期激发中华文化历史上的浩然正气,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希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而成为中国的精神脊梁,成为宝贵的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所以,士君子也是中华文化的脊梁,是中华民族刚毅奋进的灵魂之所在和代表。
我们若从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角度来看,古代所推崇提倡的士君子精神,与现代陈寅恪先生纪念王国维时所强调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其实有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①
先秦时期的孔子和儒家,强调音乐的巨大作用,指出“唯乐不可为伪”,认定“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认为一个君子的养成,必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有趣的是,西方“乐圣”贝多芬,也强调音乐(尤其是自己的音乐)“要让人类的灵魂爆出火花”!如果音乐家、作曲家自己没有“灵魂”,没有在自己创作表演的音乐作品中艺术地展现自己的“灵魂”,那他们的音乐能够让听众们的灵魂“爆出火花”吗?
“古琴艺术”申遗成功以来,古琴音乐艺术确有很大的发展,但我们在继承发扬琴乐传统时,仍需要关注、重视传统琴乐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扬,需要加强对士君子精神的认知研究,从文化自觉的高度,认真研究如何继承、赓续“士君子”的精神气质和理想,努力实现对琴乐精神文化优秀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的发展弘扬。我们呼吁必须重视民族精神和灵魂的重建,重视心灵的提升,使我们“不可为伪”的音乐艺术,能够“立人”,更让人们的灵魂“爆出火光”——这是金色的火光,热烈的火光,奋进的火光,不可不弘毅、自强不息的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