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筝乐作为广东汉乐的重要代表,是客家族群在长期历史迁徙与文化交融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传统器乐形式。它既保留了中原古乐的文化基因与音乐形态,又深刻融入了岭南地区的语言风俗及地域文化特质,逐渐形成独特的音乐审美特征与艺术表现体系。本文以客家筝乐特有的板式结构、调式类型、音阶体系及演奏技法等艺术风格为切入点,并通过考察历史迁徙、地域封闭环境、语言习俗和音乐文化传承等多重因素,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客家筝音乐风格形成的原因,以期为客家筝音乐的传承与学术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参考路径。
一、客家筝乐的艺术风格及特点
客家筝乐风格的形成与其独特的音乐表现手段密切相关。以下从调式音阶、调式类型、演奏技法三个方面,系统梳理和阐释客家筝乐的风格特征。
(一)南北地区“杂糅性”调式音阶
客家筝乐的调式音阶表现出明显的中原传统与岭南音乐融合的特质,形成了“硬线”“软线”与“反线”三种典型的音阶系统。
其中,“硬线”音阶为: (合)、
(合)、 (士)、1(上)、2(尺)、3(工),
(士)、1(上)、2(尺)、3(工), (乙)、4(凡)为装饰性经过音偶尔点缀出现,整体曲风明朗、跳跃,适用于表现豁达明快的情感场景,其经典代表曲目即《玉莲环》《绊马索》《落地金钱》《熏风曲(中板)》四首,合称“四大硬”或“玉绊金风”。
(乙)、4(凡)为装饰性经过音偶尔点缀出现,整体曲风明朗、跳跃,适用于表现豁达明快的情感场景,其经典代表曲目即《玉莲环》《绊马索》《落地金钱》《熏风曲(中板)》四首,合称“四大硬”或“玉绊金风”。
“软线”音阶为: (合)、
(合)、 (乙)、1(上)、2(尺)、4(凡),
(乙)、1(上)、2(尺)、4(凡), (乙)、4(凡)为“硬线”中的
(乙)、4(凡)为“硬线”中的 (士)、3(工)升高半音,构成微降
(士)、3(工)升高半音,构成微降 、微升4。同时,
、微升4。同时, (士)、3(工)较少出现,并作为装饰的经过音。整体呈现出细腻哀婉的音乐风格,经典曲目包括《出水莲》《昭君怨》《崖山哀》《雪雁南飞》,合称“四大软”或“莲怨哀雪”。
(士)、3(工)较少出现,并作为装饰的经过音。整体呈现出细腻哀婉的音乐风格,经典曲目包括《出水莲》《昭君怨》《崖山哀》《雪雁南飞》,合称“四大软”或“莲怨哀雪”。
“反线”音阶通过在原有“硬线”音阶的基础上进行五度转调,形成独特的调式变化模式。其中,遇4(凡)需升至5(六),遇 (乙)需升至1(上),从而保持“硬线”的调式框架并实现音阶转换。例如,经典乐曲《柳叶金》即展现了这一特点,其不同版本分别采用五次转调,即正反乐谱的第一个音依次为2(尺)、6(五)、3(工)、1(上)和5(六),依次形成商(尺)—羽(五)—角(工)—宫(上)—徵(六)调式的连续转换。
(乙)需升至1(上),从而保持“硬线”的调式框架并实现音阶转换。例如,经典乐曲《柳叶金》即展现了这一特点,其不同版本分别采用五次转调,即正反乐谱的第一个音依次为2(尺)、6(五)、3(工)、1(上)和5(六),依次形成商(尺)—羽(五)—角(工)—宫(上)—徵(六)调式的连续转换。
这种五度关系的循环移调,使得《柳叶金》的五个版本亦被称为“五调朝元”,展现了客家筝乐在调式结构上的高度灵活性。
通过表演实践与实地采风来看,笔者认为,客家筝乐的调式音阶呈现出南北地区“杂糅性”的艺术特色,特点有二:其一,中原调式融合岭南音乐特色,中原五声音阶传入岭南地区,作为基础音阶长期使用。而岭南音乐结合了中原五声音阶并融合客家民间音乐文化,衍生出微降si( )、微升fa(4)的加入。“当代广东音乐家陈德钜所著和教授的《广东乐曲构成》(20世纪上半叶成稿)中,根据民间音乐实践,确认了由原为“宫不成宫,徵不成徵”中的si(
)、微升fa(4)的加入。“当代广东音乐家陈德钜所著和教授的《广东乐曲构成》(20世纪上半叶成稿)中,根据民间音乐实践,确认了由原为“宫不成宫,徵不成徵”中的si( )和fa(4)所构成的乙凡调的特殊调性。他把乙凡调中的si(
)和fa(4)所构成的乙凡调的特殊调性。他把乙凡调中的si( )和fa(4)的音高标记为“
)和fa(4)的音高标记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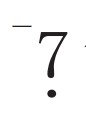 ”和“
”和“ ”,其中“
”,其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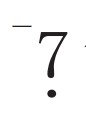 ”表示在“
”表示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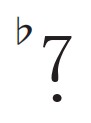 ”和“
”和“ ”之间,“
”之间,“ ”表示“4”和“
”表示“4”和“ ”之间;也就是说“
”之间;也就是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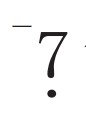 ”和“
”和“ ”都居于十二律的夹缝中,也就是从十二律分化出来的音。陈德钜所创造的符号表述法,为si(
”都居于十二律的夹缝中,也就是从十二律分化出来的音。陈德钜所创造的符号表述法,为si( )和fa(4)给予了形象的高音定位”①。
)和fa(4)给予了形象的高音定位”①。
因此形成了带有中原调式音乐的“硬线”,岭南地方音乐特色的“软线”,曲调结构、板式、旋律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向上纯五度转调的反线。呈现出南北杂糅的特点,展现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
其二,中原调式音阶接受岭南音乐的“变易”。中原调式音阶中的7(变宫)、4(清角)作为偏音的出现,在其传入岭南以后,其 (乙)、4(凡)变易为1(上)、5(六)。
(乙)、4(凡)变易为1(上)、5(六)。
这种“变易”源于民间变奏手法,在保持正调的结构、板式、旋律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音程移位,演变为另一种曲调。原曲调称为正调,移位后的曲调称为反调。这种变奏手法十分普遍,展现出悦耳的音效。
(二)脱胎于河南大调曲子的“八板体”
客家筝乐的调式主要分为“大调”与“串调”两类形式。“大调”继承自中原音乐传统的“八板体”,标准形式为八个乐句,每个乐句有八拍,第五句常增加四拍作为特征性乐句,共六十八拍的结构(俗称68板)。整体风格明亮、典雅、欢快。“串调”则较为自由,篇幅灵活多变,多由广东汉剧音乐、地方民间曲牌及民歌改编而来,注重气氛的营造与渲染,曲体形式相对松散灵活。
相同的是客家筝乐继承了河南大调曲子的“八板体”,标准句式呈现出八个乐句、共计68板相同的元素。不同的是河南大调曲的板式结构以前六句为八个板,唯有第七句以9个板位打破平衡,形成结构张力,紧接着第八句以7个板位恢复平衡,再接4个板的落句,取得圆满终止。客家筝乐在结构上遵循八个乐句的特色,但也呈现出岭南自身特色,结构相对自由。
河南大调曲子为固定板式:第一句:3+2+3,第二句:3+2+3,第三句:4+4,第四句:4+4,第五句:3+3+2,第六句:4+4,第七句:9,第八句:7+4。客家筝曲以六十八板的曲牌为规范,其产生曲牌延伸或缩短的变体,如筝曲《有缘千里》(七十六板)、《将军令》(九十六板)、《蕉窗夜雨》(三十一板)、《百家春》(四十八板)等,虽然乐曲的节奏、规律不统一,但都属于大调曲牌。以《将军令》(九十六板)为例,句式结构为第一句:4+4,第二句:3+5,第三句:4+4,第四句:7,第五句:7,第六句:6+4,第七句:4+4,第八句:4+4,第九句:4+4,第十句:4+4,第十一句:4+4,第十二句4+4。
(三)演奏技法特征
客家筝的演奏技法以右手弹拨、左手按弦为基础。右手演奏技法常用“勾托”“大撮”“花指”。通常以先勾后托、勾托同时发音的“大撮”起板,大撮还会用于句中、句尾,增强旋律的厚度,使音响更加低沉饱满;客家筝中的“花指”称为“拂弦”,一般拨动三根琴弦,作为装饰音使用频率较高,很少运用长花指。多用于乐句连接,通常贯穿于慢板、中板,增添了旋律的流动性。
笔者认为,使用其指法原因为三点:其一,与客家人民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指法的简单如同客家人居住于山区,使其有着淳朴的品德。其二,简单不花哨的指法衬托旋律古朴雅静的风格。其三,这些指法的运用相比其他流派有着岭南地区独有特色。
客家筝的演奏风格极为注重左手技法的表现力,尤其是上下滑音、颤音技法的运用,演奏者通过对按弦力度、密度的精细控制,使旋律展现出丰富的动态变化,体现出客家筝曲的古朴韵味,从而赋予客家筝乐以婉转含蓄、细腻悠远的音乐风格。左手技法体系不仅增强了客家筝音乐的表现力,被视为客家筝音色塑造的灵魂所在。
此外,客家筝乐的变奏手法也同样独树一帜。其呈现特点为:“减字”与“加花”技法的灵活运用,客家筝早期主要采用工尺谱记录旋律的骨干音,而未记录准确的节奏型,因而演奏者在具体演奏过程中需依据旋律逻辑进行二次创作。
在快速的中板乐段中,演奏者可采用“减字”技法,省略部分装饰音,使旋律更加简洁凝练;而在慢板乐段中,则可通过“加花”技法,适当加入装饰音或辅助旋律,以增强音乐的表现力与层次感。客家筝常用切分节奏型加花变化,“切分”突破了旋律的常规感,加强乐曲的变化与动感,使作品更加生动。
二、从文化角度分析客家筝乐艺术风格的形成
客家族群自中原南迁至岭南,经历了长期的文化交融与适应,形成了独特的音乐体系。以下对其风格的文化生成路径进行讨论。
(一)历史变迁与客家筝乐的文化承载
客家筝乐的产生与客家族群的迁徙历程息息相关,其音乐特征深刻映射出客家人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不同于“河南筝”“潮州筝”“浙江筝”“闽南筝”等以地域命名的筝乐类别,客家筝并不直接归属于某一特定地域,而是与流动性极强的客家民系密切相关。“客家”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汉族的多次大规模迁徙造成的。
“客家”一词来源于客家研究的奠基人罗香林先生的学术研究,其最初指的是外迁至他乡的汉族群体,后逐渐成为特定族群的称谓。根据史料记载,客家人的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期,他们的祖先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中原地区,因战乱及社会动荡,自晋代起开始南迁,历经五次大规模人口流动:晋代衣冠南渡、唐代安史之乱、宋室靖康之变、明末清初的移民潮、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再迁徙等。
这些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仅塑造了客家族群的独特文化形态,也影响了其音乐文化的发展。客家人将中原古乐的传统带入岭南地区,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与当地的音乐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筝乐体系。
(二)地域环境、语言及地域文化的影响
客家筝的音乐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客家族群所处的地理环境影响。客家人主要分布于粤东北(梅州)、闽西(龙岩)、赣南(赣州)等地区,这些区域多为丘陵山区,地势相对封闭,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生态环境。在这一背景下,客家音乐较少受到外来音乐风格的强烈冲击,较完整地保留了中原传统音乐的特征。同时,由于客家人长期生活在山区,音乐风格趋于朴实典雅,旋律线条流畅自然,节奏稳健,音色上也表现出清澈、悠远的特征。
客家筝乐的旋律风格与客家方言的语音特征密切相关。客家话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的官话类方言之一,语调清晰、发音圆润,具有较强的歌唱性和旋律感。这一语言特点直接影响了客家筝音乐的旋律特征,使其在曲调的行进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起伏性和韵律感。此外,客家文化中的礼仪习俗、岁时节庆等也对筝乐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三)广东汉乐传承对客家筝的影响
客家筝乐的发展离不开广东汉乐的深厚文化背景。广东汉乐是一种融合了中原古乐、南方民间音乐及戏曲元素的传统音乐体系,广泛流行于广东、福建、江西等地。以梅州市大埔县为代表的广东汉乐汲取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并在南方语境中演变发展,最终形成独特的地方音乐风格。明嘉靖九年(1530年)《大埔县志》记载:“埔之在潮,弦诵媲邹鲁,家诵户弦”,可见明清时期大埔地区弦乐演奏的繁盛局面。广东汉乐有五种主要演奏形式:丝弦乐、清乐、中军班、汉乐大锣鼓、庙堂音乐,其中丝弦乐与清乐对客家筝乐的形成影响最为显著。
客家筝曲的曲目主要来源于丝弦乐和清乐。丝弦乐,又称“和弦索”,以头弦领奏,配以提胡、扬琴、琵琶、筝等乐器进行合奏;清乐则以古筝为主,辅以琵琶、椰胡、洞箫等乐器,被称为“筝琶胡”组合。这种音乐形态的传承,使得客家筝乐既具备广东汉乐的典雅特质,又保留了自身独特的音乐风貌。
(四)重要人物的影响
何育斋:客家筝乐的奠基与体系化构建
何育斋(1886~1943),是客家筝乐体系化构建的奠基人。他在曲目整理、记谱体系完善、技法规范化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20世纪20年代,何育斋开始系统整理广东汉乐曲目,编订《中州古调》23首、《汉皋旧谱》37首,避免了大量传统筝乐曲目的流失,为客家筝乐的曲目积累奠定了基础。
此外,他改进了传统工尺谱,创造“工尺谱谐声字谱”,该记谱法以客家方言为基础,结合南北音乐体系,使演奏者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音高变化,提高了客家筝乐的可读性和可传承性。
在技法体系方面,何育斋还总结并编创了《弹筝八法》,不仅丰富了客家筝的演奏风格,也为后世客家筝乐的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客家筝乐的演奏规范。
何育斋对客家筝的推广与演奏技法改良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30年,他离开梅州前往广州,创办“潮梅音乐社”,通过组织演奏活动、音乐交流等方式扩大客家筝乐的影响。为了适应舞台演奏需求,他对客家筝的形制进行了改良,不仅提升了筝的音量和音色,使之更适合独奏演出,也为客家筝乐的发展提供了更加稳定的物质基础。
罗九香:客家筝乐的推广、传承与流派确立
何育斋去世后,其弟子罗九香(1902~1978)承袭师法,使客家筝乐从地方性传统音乐走向全国乃至国际舞台。可以说,罗九香进一步促进了客家筝流派的形成。
1956年,罗九香与扬琴演奏家饶从举、提胡演奏家饶淑枢组成“客家音乐三人组”,代表广东汉乐参加北京全国音乐周,罗九香演奏了《出水莲》《将军令》等客家筝曲,其独特的音色、典雅的风格和娴熟的技巧赢得了极高评价。1961年,西安音乐学院召开首届全国古筝教材会议,罗九香向会议推荐39首客家筝曲,并被选编为全国高等音乐学院古筝教材。
罗九香还曾积极推动其进入高等音乐学府。1956年,罗九香受聘为天津音乐学院古筝教师。1960年,他调入广州音乐学院(原广州音专)任教,使客家筝乐正式进入广东的专业音乐教育体系。在其教学生涯中,罗九香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古筝人才,其中包括:古筝演奏家李婉芬、何宝泉、陈安华等。
结语
客家筝乐作为广东汉乐体系中风格辨识度极高的区域性筝乐,其“硬线、软线、反线”调式结构、“八板体”板式体系与岭南化演奏技法,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风格谱系。其个性化特征的生成,深植于中原古乐的文化延续、岭南民俗的地域制约与广东汉乐传承系统的技术依托。探讨客家筝乐的风格构成机制与文化生成路径,有助于推动区域筝乐的谱系梳理与多元音乐文化的学术建构。
注释:
①费邓洪主编;陈浚辉副主编:《论乐岭南: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建所40周年音乐论文集》,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340页。
参考文献:
[1]王英睿.中国当代筝乐流派之总述(四)——客家筝派[J].乐器,2022,(01):57-59.
[2]袁莎.客家筝艺流派的形成及演奏特点[J].乐器,2017,(12):42-45.
[3]刘燕.客家筝考[J].中国音乐,2005,(02):104-107.
[4]刘思思.浅议客家音乐对客家筝的影响[J].乐器,2013,(09):42-44.
[5]尹璐.客家筝乐的文化属性及其审美特征研究[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0,(04).
[6]陈安华.音乐学府中教授客家筝的第一人——纪念著名客家筝代表罗九香大师九十诞辰[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2,(01):13-16.
[7]罗伟雄.“客家筝派”本源论萃.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06.
[8]何松.何玉斋筝谱遗稿.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2002:95-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