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写作建立在田野考察基础之上。所谓“音乐生活”是通过生活入手,既希望从较为全面的文化角度来勾画石龙村的音乐生活,也希望以民间艺人的活动来描述音乐生活在一个村落中的意义,以及音乐生活对于该村落传统文化构建的作用。
[关键词]白族;石龙村;音乐生活
作者简介:杨曦帆(1969—),男,四川成都人,复旦大学艺术人类学专业在站博士后,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艺术人类学。
原文载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9年第三期
石龙村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沙溪镇所辖的一个行政村。在剑川县城西南25公里,南距沙溪镇政府20公里,石龙村以北即是纳西族聚居地丽江,站在距离石龙村四公里的石宝山大门处可眺望80公里外的玉龙雪山。
目前,云南大学在石龙村开设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基地;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在石龙村建立了白语学校。北京、昆明等地部分高校民族学、语言学等专业有研究人员在此从事或长或短期的田野调查。这些学术机构在石龙村设置研究基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石龙村的民俗文化在白族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作为“文化村庄”的石龙村
石龙村所属县治剑川在云南素以文化著称,与大理、石屏共享“文献名邦”之美誉,是清代学者赵藩的家乡。①剑川全县人口16万余,白族约占92%,是全国白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所属沙溪镇为著名的“茶马古道”古镇,历史上是茶叶等名产运载以及佛教僧侣往来的重要通道,距离石龙村六公里是建于南诏(738-937)和大理国((937~1253)时期以石钟山石窟寺而著名的佛教圣地。
关于石龙村村名有如下传说:
相传有一天在石宝山上举行法会,突然狂风把会幡刮走,法师令人追踪会幡,结果翻过山坡发现一个小坝子,坝子里有山有水,土地平坦,森林茂密,四周高山环抱,会幡就挂在树上,故取名曰“挂纸坪”。“挂”白语叫“蕨菜”,“纸”白语是市场的意思,“挂纸”和白语“蕨市”同音,于是又称为“蕨市坪”。②一百年前,石龙村张耀彩到沙溪坝做客,记帐先生把“蕨市坪”记为“绝世坪”,张认为有侮辱之意,回村后就把村名改为“石龙村”,取意于石宝山边卧条龙的意思。
石龙村平均海拔2628米,过去一直是全县高寒贫困山区之一。2002年确立为剑川县“温饱示范村”,目前温饱基本解决。2007年人均纯收入达1207元左右,主要来自种植业、养殖业和野生菌加工。由于贫困,石龙村一日三餐过去是“一稀二干”(一顿稀饭,两顿干饭),现在三餐都可以吃上干饭,这对于贫困山区的“温饱”是个重要指标。石龙村现辖一个自然村,三个村民小组,共234户,1093人,劳动力710人(2007年)。分属白、彝、傈僳三个民族,其中,白族占90%以上。③
在文化教育上,村民教育程度低,高中、大专文化占2.8%,初中文化占18%,小学及以下占78.5%。但是,体制内教育的不足并没有妨碍石龙村自我文化的生长与发展。目前,石龙村民间文化组织有老年协会一个,会员84人;洞经会一个,会员14人;“妈妈会”一个,会员80人。有关部门现在正组织打造“白族文化生态村”。
从石龙村的空间结构来看,传统的文化空间基本位于该村村口。在进村的路上,绕过“石龙水库”,远远就可以看到一面比其它房屋高出很多的白墙,里面是“本主”④庙和其正对面的戏台。每逢节日,老乡都要在这里祭祀“本主”,过年的时候则有“乡戏”表演。石龙村另一个文化中心在“村委会”(当地人更习惯用以前的称谓“村公所”)对面的广场上,新建广场有一个装配了音箱的舞台。这里在火把节的时候成为全村的中心,参加火把节的主要是本村的年轻人。
村公所是全村的政治中心。村公所隔壁是卫生室,斜对面是小卖部,小卖部门口从早晨开始直到夜幕降临常常会坐着几位老年人,有时候也会有中青年男人。坐在那里的人或者是聊天、或者是打牌,有时候也喝酒。80岁出头的张定鸿和他70岁的弟弟张定坤,还有60多岁的董佳兴等老年人是那里几乎每天都去的“常客”。这样,在小卖部门口似乎无意识地形成了一个老年男性空间。这个空间在全村的地理位置上很重要,所在地是石龙村进出的必经之路。坐在这里,不仅可以作为观察者观察到所有人进出,也可以让其他人意识到这些观察者的存在。这些男性大多已经参加了本村的洞经会或者是拜佛会,他们中的人要么是会某种乐器,要么是长于诵经。他们在一起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是下一次去什么地方做法会。
二、石龙村的信仰与传统音乐文化
1、信仰
石龙村的宗教信仰比较复杂,全村中年以上男女,尤其中老年女性多加入佛教会和“妈妈会”。史书称白族信佛,“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参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1]石龙村一带的信仰除了佛教信仰之外还存在民间信仰,比如,白族传统信仰本主崇拜在石龙村就很重要。村民把本主当成保护神,凡遇疾病灾祸都要请求本主保护。每年大年(正月)初五是“本主”诞辰,要举办乡戏,同时除夕夜、大年初一等全村人都要到“本主”庙进行供奉,祈求平安。民间信仰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信仰更民间化。位于石宝山最高峰(海拔2720米)的金顶寺寺内没有驻寺僧人,只有一个中年男子看护寺院(已看护三年)。据介绍,金顶寺每年“热闹”两次,一次是农历正月初一到初八,另一次就是石宝山歌会期间的拜佛活动。金顶寺的信仰活动主要由当地巫婆操持。从文化属性上讲,金顶寺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当为民间崇拜。其主殿一楼供奉从左到右是关公、观音、文昌;二楼供奉玉皇大帝。该寺最初建于清康熙年间,约距今30年前重建。
总体看来,佛教的重要性在今天的石龙村主要表现在四周的寺院建筑、石窟艺术和历史记载中。今天,信仰中的年龄层次已经表露出这里不再是全民信教的地方。石龙村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是不可置疑的。这也使它具有原始宗教特征的巫术行为在信仰活动上相对于彝语支其它民族要少,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白族人的宗教生活中明显地包含着强烈的儒家因素。在信仰中“儒教”成为核心,孔子的地位得到强调并以此作为民间文化之正统。所以,尽管有时候表面上是打着佛教的名义,但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表现出农耕社会所常有的“三教合一”乃至包含“本主”崇拜在内的景象。既服从佛教会的三规戒律,家中又设有祖宗堂,供奉天地君亲师、灶王和祖宗。逢农历初一、十五吃素,每年大年初一、六月六、九月九等都要参加村里举行的法会。在涉及信仰中的音乐活动时,也主要是由与道教文化有关的洞经会来完成。
2、洞经音乐会——传统的力量
石龙村自发组织的有洞经会,大约成立于1950年,由诵经队、古乐队组成,每逢农历六月六、九月九、村里及附近老人去世等时,洞经会都要做三天三夜的法事。被大家看作是石龙村儒家文化领袖的洞经会会长张灿兴⑤阐释过石龙村洞经会的信仰主张。石龙洞经会属于“儒教大洞祖师文昌皇人”,故此儒教涵盖佛教、道教,而属于儒教文昌皇人的洞经会自然也可涉及所有的信仰门类而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尽管在本主节上他也要去本主庙,但所有的一切,按他的说法,都统归在“儒教”这一大旗之下。这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对于儒、释、道的理解。

图1、洞经会成员董佳兴、姜路宝
以儒家的方式阐释信仰生活,对于音乐行为空间来说,导致的具体现象就是洞经会的普及。这种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生活方式在白族地区由来已久,这也和白族的族群结构有关。当地文人撰文描述过20世纪40年代的生活场景:“上街场西有三圣宫,供刘备、关羽、张飞,平时村中演奏洞经音乐,绅士老爷们聚议村政大事,都在三圣宫。”[2]这说明,支撑信仰的传统文化同时被作为一种权力与身份的象征,这二者之间有着很内在地关联。
据了解,石龙村的洞经会没有固定排练时间,基本上也无乐谱传承,这和洱海地区如三文笔村的洞经会有区别。目前能够演奏的曲目主要有“开经偈”、“众等归一”、“双男子”、“一心奉情”、“仙家乐”、“取经藏”、“弟子众”等。洞经会现在有成员14人,年纪最大者(张文坤)71岁,最小者(张万洪)53岁。使用的乐器主要有:二胡、京胡、低音二胡、三弦、笛子、唢呐、钹、锣鼓等,另有专人念经。主要在“孔子诞生”、“观音会”、“拜灶君”等活动中使用。在使用功能上,“剑川白族洞经音乐除了用于道教科仪外,还用于民间‘做会’。”[3]
洞经会的存在显然让石龙村的文化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而有趣,这使得石龙村不仅仅只是一个惯于“耕种”的村落。从文化的角度讲,“耕种”还可以分化为“耕读”与“种田”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尽管都是劳作于大地。但“耕读”显然是含蓄地隐喻了某种可以超越于土地的文化冲动,也正是有着这样的文化动力,才可能构建一个具有文化意味的村庄,也正是因为有了文化上的分层才会有石龙村音乐生活的丰富性。在这样的“文化”含义浓郁的村庄里也才会有洞经会,才会有一年一度自发的演戏,才会涌现众多的歌手,以及乐器演奏的普遍性。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角度来看,“耕读”连贯着作为“大传统”的儒家文化和作为“小传统”白族民风民俗。
3、传统音乐文化中的妇女
妇女在石龙村总是很繁忙,她们从早到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做。就笔者观察所见,妇女较少聚集在一起闲谈,也几乎没有妇女会使用乐器。但是,白族妇女以长于歌唱而闻名。有一次我请一位当地有名的女歌手唱白族调,她很为难,显然,她不愿意在家里,或者说是在村子里唱歌。后来我跟随她一起上山“打草”⑥,当我们在雨中坐在山坡休息时,她主动唱起山歌。歌声在山野间听起来异常亲切。这就是石龙的歌声,在本源的意义上,它不存在于村寨,只存在于山野。远处也传来歌声,尽管没有刻意对歌,但原本寂静的山间似乎突然就丰富起来,田野中的山歌,和寂静的村寨形成了鲜明对比。还有一次,我在另一位歌手家。她和他丈夫比较开明,她愿意在家里唱白族调。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她的大哥从山上采菌子下山路过、顺便来吃饭。歌手立即跑回厨房开始忙碌,并低声告诉我,大哥来了,现在不能唱了。当我好奇地追问“为什么”的时候,她含糊地说,“在家唱歌,让大哥听见影响不好。”显然,某种力量仍然能够比较有效的维持传统观念。那些坐在小卖部门口的老年人很有可能就是这种“力量”的符号。尽管公路已经修到村内,但传统依旧在“掌握”之中。只是这种“掌握”更可能是一种隐藏着的惯性。这也说明,音乐生活的丰富与多元性后面隐藏着社会文化结构的多元性与多层性。
从这样的村落结构来看,传统文化不仅有着“传统”本身的惯性,同时也有着局部的重构。比如,为火把节新修的广场和戏台(实际上,我住在石龙村的时候就一直琢磨这个建筑应该叫“戏台”还是更应该叫“舞台”。这两种不一样的称谓显然的有着不一样的指向)。“妈妈会”是专属于妇女的,也称“莲慈会”。据当地人讲,石龙“妈妈会”一百多年前已存在,女人年过50岁绝经后可入会,表示人已“干净”,可敬神。在各种大小法会都可参加诵经,主要是集体拜诵“老皇经”、“新皇经”、“佛经”等。“妈妈会”的活动场所主要在村头的本主庙,有时也在私人家中庭院或者是特定节日类场合。其腔调抑扬顿挫,节奏舒缓,每人一个小木鱼,一面念经一面敲木鱼。
4、石龙村的霸王鞭舞
霸王鞭舞广泛流传于白族地区,但石龙霸王鞭舞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和艺术风格独树一帜。石龙“霸王鞭”的来历已无从考证,但代代有传人,一般在火把节晚上表演,舞蹈有乐器伴奏,多是一人拉胡琴或弹三弦。舞蹈可独跳亦可群舞,或围着火把绕圈跳,或分四角循环,在一角表演后又舞到另一角表演。

图2、石龙村霸王鞭舞
据了解,石龙霸王鞭舞以前由男性表演(改革开放后发展成女人也可跳,而现在则基本成为女性表演的节目),可边舞边伴唱本子曲,也有乐器伴奏。过去舞者持鞭方式别具一格,手持霸王鞭尾部(其它霸王鞭都持中间),使道具的运用更为灵活。但现场看,似乎也是握在中间部分,只是不像洱海地区那样完全握在中间。一般认为,石龙村的霸王鞭舞与洱海地区霸王鞭舞有一定区别。根据伍国栋教授80年代在剑川地区的观察,也认为剑川霸王鞭舞的舞者“舞蹈时,舞者手握鞭之三分之一处(不像其它地方是握在正中),动作低矮,活动场面较大。”[4]185图中左二舞蹈者为六十多岁的张佳祥,年轻时擅唱白族调,中年以后主要跳霸王鞭舞。
现在,每年的农历6月25日举办火把节,竖火把、跳霸王鞭舞、唱白族调是石龙村重要民俗活动之一。从民俗角度讲火把节主要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据介绍,目前石龙村霸王鞭保存有三套:“观音扫地”、“双飞蝴蝶”、“童子拜观音”。其动作有“双肩奉送”、“八步梅花”、“左插花、右插花”、“八面威风”等20多个。
从功能角度结合当地研究人员介绍,石龙霸王鞭舞与当地的白族生产生活关系较为密切,长期形成的劳动习惯动作自然而然地交融于舞蹈动律中。目前,霸王鞭舞被分成老年人和青年人也说明了文化的原生态和再构建之间的差异。我住在村公所的日子里,很多个晚上都有村上组织的青年妇女在村公所院子空地上学习霸王鞭舞。不过,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对此并不熟练,她们的生活中已经逐渐不需要霸王鞭舞,学习霸王鞭舞既是“任务”也是为了让外面来的客人觉得“文化生态村”的人仍然是能歌善舞的。
5、石龙村的“乡戏”
据当地人讲,石龙戏班成立于1945年,有戏师、画脸谱师、化妆师、乐器组、戏衣箱等。主要在过年时演出,且多数是在本村自演自唱自欣赏,也有到外村演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县内其他各戏班大都已解散,但石龙村的乡戏却保持了下来,据说是全县唯一幸存的村级戏班。所演“乡戏”据了解即为滇剧,因在乡村演出故称为“乡戏”。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乡戏”也可理解为不进入消费环节的,“自产自销”的娱乐形式。
石龙村的乡戏所有演员都由本村中老年男性村民组成,乐器包括:胡琴一把、唢呐一支、鼓、钹、锣各一。演出中,鼓师掌控节奏。在现场,有一中老年村民不穿戏装蹲在台上手拿戏本小声念白提醒演员台词。戏台正对本主庙。妇女们在本主庙里唱诵经文,20米开外的戏台上业余演员们自我陶醉地唱着乡土戏,观众同样由本村村民组成。实际上,更多的时候台下除了笔者这样的好奇者外,几乎没有人看戏,大家有的坐在台下打牌,有的忙于清算帐目,有的聊天。戏台上的演出和戏台一样,所起到的意义在于构建意义上的文化空间。没有人“专注地”看戏大约源于当地人少把此看做是“艺术”。这不过是节日仪式中固定的程序。
三、石龙村的歌声
1、白族调的背景
据说,石龙村的白族调普及于清朝,而石龙村邻近石宝山,村民自小就喜欢在石宝山上“对”白族调,因而歌手层出不穷。自从有歌会起,石龙村歌手便是唱白族调的主力,今天的情况亦不例外。在石宝山赛歌会上,获奖者多为石龙村歌手。白族调从类型上讲有本子曲⑦和情歌二种。唱词格律为“七七七五”式,俗称“三七一五”体,每节歌词以三个七字句和一个五字句构成,四句为一小段,若干段组成篇。
白族调多为五声羽调试,其乐段变化常见的是反复二段体结构,在演唱上男女声均以真声演唱,以剑川为代表的山区白族调则用三弦伴奏。[5]白族地区三弦可分为龙头三弦、小三弦和弯头三弦三种。[4]156石龙村主要以龙头三弦为主,在村内也较为普及,能够较为熟练演奏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有数十人。传统上,三弦只限于男性演奏,现在也有个别女性开始学习三弦。目前,龙头三弦独奏曲所知的主要就是在剑川本地比较流行的“剑川白族调”等。
石宝山歌会是石龙村白族调重要的表演场所。石龙村的歌手更可能是因为石宝山歌会的传统而存在,是一种民间的文化传统创造了石龙村的歌手。也可以这样说,传统创造歌手,也创造了歌手们的生活。在整个石宝山,歌手最多的就是距离石宝山两公里的石龙村,而其它村子的歌手则很明显的少很多。
2、民歌手的舞台——石宝山歌会
剑川石宝山自古以来每年农历7月底、8月初,远近各州县白族人都要聚集在佛教圣地石宝山下对歌唱曲。对歌会与白族“阿吒力”⑧佛教法事活动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哪怕是在更高更远的金顶寺中,也在歌会期间有重要的祭祀活动。
在强调禁欲的宗教圣地举办具有男欢女爱性质的情歌对唱,这本身在信仰民俗上就包含着强烈的反差。从空间上看,中老年妇女多上山前往寺院拜佛,青年人则在山下空地对歌。对歌主要就是指男女对唱情歌。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对歌是男女青年相识恋爱的重要环节。在现代社会中,年轻人可以更广泛地获得寻求爱情的机会,而不必像他们的长辈那样把婚姻寄托在对歌会上,这也逐渐使得对歌会上的对唱情歌成为一种与现实爱情世界不相干的活动。现在,已婚者参加对歌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这反映出当今对歌会还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之一,是因其满足了人们期望有机会与配偶以外的人在特定时空下进行的哪怕是精神上的恋爱。或者说,对歌会成为了一种公认的合情合理的时空,在此期间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情感略加“放纵”——当然,就所能见到的情况来说,这种“放纵”主要是以隐藏在歌声中的方式进行的。在白族人心理上,涉及崇高意味的宗教活动和涉及情爱的对歌民俗活动之间似乎可以变通统一。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是民歌手,在年老的时候则成为宗教徒。就此或可理解,宗教与生活之间原本是互溶的,作为秩序的对立源于人的想象和社会行为的逐步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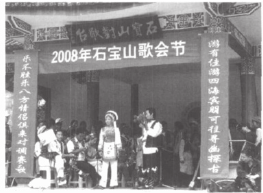
图3、石宝山歌会
石宝山歌会作为一民俗活动源于石宝山香会,即男女信众进山敬香朝拜。当地学者认为“石宝山朝山,应始自石钟寺佛教石刻造像雕成,因工艺的高超与宗教魅力,引来各地善信闻风而来进香朝拜。而后高僧寂定讲经,听众云集,进一步促成朝山会形成,继之寺僧每年届期斋醮,游人香客不约而渐衍成俗,青年男女亦因赶热闹缤纷杂沓,年复年,随着世风演变,游人发生谈情说爱,伴随之弹弦对歌,即演成民族风情浓郁的石宝山歌会。”[6]根据此例,从民俗学角度还可判断为,“这些歌会还带有明显的原始时代遗风。首先,歌会不避男女,大家齐上歌场对歌的群体参与方式与氏族社会男女混杂、不拘礼法的居处方式相等,而与封建时代家族制度基于‘血缘’‘贞操’的封闭观念相左。其次,从歌会的内容来说,体现了氏族社会男女之间以歌相悦、对歌寻偶的遗俗。”[7]所以,白族当地学者张文认为“歌会历史悠久,源于‘群婚’上古遗风”。[8]此说应当有理。《云南志略》也称:
处子孀妇出入无禁。少年子弟号曰妙子,暮夜游行,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韵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耦,然后成婚。[1]
另外,石宝山石钟寺内地“阿央白”⑨崇拜也可视为与性俗有关的一种民间传统,到石宝山来参加歌会的妇女多要来此烧香,以求子嗣。
针对石宝山歌会做过调查的日本学者指出,“现在的歌会已与佛教祭祀活动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在歌会上男歌手唱道:“不是拜佛来朝山,我为采花到这边。”他还认为“石宝山歌会是白族青年在佛教祭祀活动时集中到一起寻求异性伴侣的歌会。现在,相对于歌会的盛况来说,人们在石宝山的佛教祭祀活动表面上已经淡化,根据笔者亲眼所见,来石宝山寺院拜佛的多数是年长的妇女,其他大部分人是来欣赏对歌台的对歌比赛和对歌台前广场上的歌舞表演的。”[9]也就是说,这类乡村“情人节”和宗教活动,原始民俗与儒释文化的同时出现使得石宝山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多元立体地带。显然,这种把信仰和民俗活动统一在一个时空中进行的传统,不仅可以更加方便的聚集更多的人群而且可能对于各自不同的文化元素有着整合作用。从历史发展角度看,现在乐意上山拜佛的中老年妇女实际上在她们年轻时也是热衷于参加对歌的。当然,男性也是如此,正如老年人说的那样:
年轻时也唱白族调,唱风流歌;年纪大了,有儿子孙孙了,就念经、唱戏读圣贤书了。(笔者采访笔录)
随着时代的演变,今天的石宝山歌会已经成为一个政府组织的民间民俗文艺活动。在歌会开始前几天,宝相寺一带就开始云集各式商铺,有卖各种餐饮、各种首饰的小店,又有各种游戏,如扔沙包打中礼物等,十分热闹。由于已经演变为政府行为,歌会开始有开幕式,大理州州委书记等官员到场。开幕式上是李宝妹等成名歌手表演。在石宝山歌会上诞生的“有名歌手”就是指能够在对歌台上一直对歌的歌手。很多歌手对上几句就语塞败阵,总体上看,良好的乐感和语感,丰富的生活体验,随机应变的能力,是一个成功歌手的必要条件。
下午开始对歌比赛,参赛歌手以石龙村为主。一位小有名气的女歌手由于只得了优秀奖,对于这个结果显然是不满意的。另外两个也是优秀奖的男歌手和她一起把刚到手的奖状就在对歌台旁撕了。当然,他们还是很注意地把写有自己名字的部分或者是撕得更小或者是拿走了。对歌比赛的名次对于尽管是业余歌手们来说也被看得很重要。“音乐生活”尽管从生产方式上对于大部分石龙村人来说只是业余生活的一部分,但无论在传统状态下还是在现代社会中,这可能既关系到他们今后的“出场费用”,同时也是一个“面子问题”。
据当地人介绍,今天的石宝山对歌不如以前热闹。白天只有比赛,真正地自由对歌要在晚上才有。笔者晚上在宝相寺一院落内观看了来自沙溪的民间艺人黄四代对歌演唱。当地男女各坐两侧听歌,以年纪大者居多。有洱源县大树乡女性二人与黄对歌。每听见观众会心笑声,想必就是精彩处了。黄四代认为一个唱白族调的民间艺人应具备以下条件:爱好;乐感好;声音好。还指出,不同地区的白族调在演唱风格上的区别:大理地区白族调拖腔长;剑川地区白族调音腔干脆;兰坪地区白族调拖腔长而凄厉。晚上十点左右,约二十多个小伙子涌入院内,旁边的当地朋友告诉我,这是来找“姑娘”的。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用歌唱来找情人,而有点像美国西部片中的牛仔。所以,“情人节”期间,发生打架现象是不奇怪的,这也是“音乐生活”的一部分。石宝山歌会一共办三天,其实在第一天后,人群量明显减少。第三天下午是决赛,石龙村有名的歌手李根繁得了第一名。
3、石龙村歌手的生活
石龙村与石宝山歌会之间有着互动关系。不仅因为石龙村歌手是每年石宝山歌会上的主力军,而且很多石龙村歌手也是通过石宝山歌会而出名,成为大理、乃至云南著名歌手。石龙村中能够以演唱白族调作为主要或部分谋生手段的大约有10人左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李宝妹。中央电视台曾拍摄《石宝山上的百灵鸟——李宝妹》电视专题片,另录制多张CD、VCD由云南民族音像出版社出版。白族学者张文对李宝妹的艺术能力有如下判断:“首先,李宝妹具有独到的演唱和即兴编唱白曲的创作才能;其次,其演唱风格突出,独具韵味,充满朴素之美。”[10]
除了李宝妹(现为剑川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其他大多数歌手都不脱离农村的生产劳动,唱白族调主要是夏天和春节农闲期间在外面去唱,其它时间都还是在务农。他们大多都只有小学或是初中文化,务农除种田外就是采菌子。采菌子是石龙村农民最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民歌手们还可以比其他人多一份收入来源,这就是他们受邀请到“外面”去唱白族调。“外面”主要是指剑川县其它乡镇,大理州内其它县,怒江州兰坪白族自治县,也有被邀请到昆明,甚至云南省以外。
在生活上,一些歌手已经能够用歌声来获得生产劳动之外的收入。我曾经住过的一位歌手家中共五人,其中夫妻二人务农,儿子初中毕业也在家务农,女儿初中行将毕业打算上高中,还有一老母亲在家。五口人大约有六亩地,粮食除自己吃之外,卖粮收入很少。主要收入靠上山捡菌子,这样一年有大约一万元左右的收入。另外,作为当地较有名气的歌手,每年大约能够因被邀请外出唱白族调而挣七、八千元左右以补贴家用。⑩
由于石龙村存在较多的歌手(就一个村子而言),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歌手之间的竞争。比如,一位歌手就曾在昏暗的灯光下长时间向我抱怨“上面”(指县政府的文化部门)对他不够重视,在一次重要的白族歌手活动中“遗忘”了他,忽略了他在当地歌手中的地位。
总的来说,石龙村的音乐生活不仅构建着本村的传统文化,而且越来越多的在各种专业化舞台上频频亮相。以2007年为例,这一年,“白族歌后”李宝妹在2007年大理州洱海歌手大赛中获得原生态唱法一等奖,新秀“阿鹏”在云南省首届青年歌手大赛中获得原生态唱法第二名,石龙村的李根繁、李福元、张佳益参加了平安创建活动光碟制作,等等。这些活动说明石龙村的民间音乐已有相当高的程度,代表歌手的半职业化或职业化音乐活动比较频繁,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并开始由完全民间化向半专业化、专业化的过渡阶段。
4、白族调的发展——新农村文化建设与传统艺术的结合
民歌是由歌词和曲调组合而成。白族歌手能够“看什么唱什么”这种能力要经过长时间的培养,对于现实社会敏锐地观察,对于语言把握能力的不断提高。但是,音乐曲调并不是可以被忽略的部分,正是曲调的完善,才使得歌手们能够更好地表现随机应变能力和语言能力。毕竟,再优美的语言对于白族调这一特定表现形式来说,都必须要以固定的音乐形式来表现。没有对音乐的认识,就不可能理解白族调中语言上的韵味。
用白族调配以符合新时期需要的歌词是目前较为常见的事情,尤其在乡村政府组织的文化宣传活动中更为普遍,如:
加强新农村建设
各项事业齐发展
关键要保护生态
勿浪费资源
生态是身上长的肉
资源好比心脏血
如果我们不重视
要危害后代
……
从歌词内容上看,这种旧调新词基本上结合了现实社会的种种情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白族调这种艺术形式在白族民间便于传播的特点,这也可成为新农村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接轨的一个对接口。这一点,石龙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比如,石宝山白曲演唱团在李宝妹等人的带领下曾赴该县九个乡镇自办石宝山白曲演唱会。内容以宣传戒赌、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增进民族团结、弘扬新世纪新风尚为主,演出采用演员和听众互动的方式,不少民间歌手纷纷登台与演员合唱、对唱,颇受当地群众欢迎。
四、石龙村音乐生活的前景
1、输出“音乐劳动力”
石龙村丰富的民间音乐生活对于当地青少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近年来,石龙村人开始走出家门,白族歌舞也为更多地人所接受,目前已有三个20岁左右的青少年被“云南印象”选中去做演员并成了骨干,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北京、深圳、昆明、大理等地靠歌舞挣钱,这从市场化的角度看也说明这个村子音乐传统是很有根基的。随着政治经济的改革,今天的农村政治活动中,村干部的权力空间和过去相比已有了较大变化。其个人威望的形成与维持是多方面的,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个人的致富能力显然成为乡村威望的一种象征。具体在石龙村,能够通过组织活动维持石龙村音乐生活,对于村干部权威与被尊重的维持,都具有重要意义。这说明,在现代村级政权中,作为隐形的文化对于威望与权力结构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不仅涉及传统文化、精神追求,同样也涉及经济收入问题。村委会副主任姜伍发是向外输出歌舞人才的重要组织者和民间音乐的积极倡导者。五年前他就组织村里年轻歌手去其它县演出,2007年组织的火把节演出使参加演出者每人每天能挣200元,这对于还处于传统生产方式的山区村民来说还是具有相当诱惑力的。
在经济社会里,除了民歌手们之外,村里的洞经会也有相应的收入。去周边寺院参加一年一次念经、奏洞经音乐等活动,要花上7-10天,每人大约可得200-400元。相比之下,白族调在村里是低调的,但在村外则是具有很大的现代市场潜力;洞经会在村里是高调的,但显然他们距离任何市场都有着不小的距离,尽管他们很愿意把自己推向市场。但洞经会在外演出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沙溪镇。而歌手们在问及去过什么地方演出时,如果他们去过沙溪但大多不会提到这个名字——他们很多人都去过更远的地方,甚至包括昆明、深圳、北京等大城市。
石龙村作为才脱贫不久,刚解决温饱的山区村,目前大约有一百多人外出打工,其中依靠演唱白族调“以乐谋生”的大约有数十人,占外出打工人数的10%左右,应该说,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这似乎象征了“农民工”“文化进城”的可能性,为农民用手中的传统民间音乐在市场经济中创造财富提供了新的机遇。目前,石龙村外出(包括曾经外出)“以乐谋生”的人员中,年龄最小的16岁,年龄大的也就30岁左右,是真正的青年群体。他们通过自幼耳濡目染学习来的歌舞就可以挣钱找工作,甚至当明星,这对于石龙村的其他青年有着不小的示范作用,这也是石龙村民间音乐能够走上一条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因。
2、传统文化的新建构——矛盾与自觉
保护与开发从概念上讲是“矛”与“盾”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不少人也这样认为,最好的“保护”就是不要去改变它。但现实的情况在于,在“传统遭遇现代”的今天,研究人员有理由在社会变革期间以更大的热情研究民间艺术在整体社会变化下所受到的转型影响。以学术视野预见、批评、建议民间艺术在现实中的种种现状,以学术的方式思考、协调矛与盾的各种关系。
对于石龙村的民间音乐来说,由于白族有着相对较强的民族文化自信和较强大的民俗文化根基,特别是当民间音乐能够成为一种“以乐谋生”的手段时,那么,从生存意义上所认识到的民族文化的自信能够使得相应的传统艺术得以更为长久地受到“传统文化势力”的保护。实际上,近年来各类研究人员或长或短的入住石龙村已经让村民们隐约意识到自己“文化”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形成一种文化自信。也许可以这样预见,当这种民族文化的自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很有可能从“文化自信”转化为“文化自觉”,到那个时候,保护与开发这对“矛”与“盾”的关系就能够从其民族文化内部予以认识并可能给予解决。解决的方案取决于村民们如何以现代社会的视野来“重新构建”传统的文化村落,这里面既包括对传统的新的理解与塑造,也包括传统民间音乐在石龙村的延续发展,同样还包含包括笔者在内的各路研人员的研究活动对该村观念的影响。这就是说,“重构”的想象理应建立在某个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这也说明,尽管现代化对于传统文化有所冲击,但如白族这样的民族,诸如石龙村这样的村落,其中一些传统的民俗力量仍然在起着作用。
结语
总体上看,石龙村似乎存在两种不同的民间音乐力量。一种是唱白族调的民歌手,他们有机会能够外出演出,年轻一点的还可以有机会就此以歌舞为职业。另一种是中老年男性组成的洞经会,他们中有的人以前唱白族调,因为年纪大了而改为谈演洞经,有的人则是从来就只对此感兴趣。洞经会音乐很多重要仪式的组成部分,比如,白事都要用洞经,自然也就有洞经音乐,也成为石龙村传统文化的承担者和道德力量的构成因素。这两种力量实际构成了石龙村的音乐生活。
对“音乐生活”的描写意味着不拘泥于“音乐”,而是更加全面地观察音乐现象,或者说,是把音乐活动作为特定时空下人群的人类行为予以关注与研究。以田野工作的方式来理解一个村落的音乐生活,表明民族音乐学之田野工作本身还不仅仅是一个当下性的观察问题,同时也是一种对研究对象之历史性“构建”。也就是说,“对于乡间民间音乐生活的关注并不是一种完全的猎奇式的打量,而是一种全景式的历史书写。”[11]民间的音乐生活并不是没有历史,只是大多没有留下书面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隐藏于生活之中,田野工作就是以“解读”的方式接近生活而使“沉默的历史”获得一种新的机遇。
引文注释:
①清人赵藩因在成都武侯祠题撰名联而闻名:“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②明代游侠徐霞客在《游记》中把石龙村称为“蕨食坪”,清《康熙剑川州志》称其为“蕨市坪”。
③数据由石龙村“村委会”提供,下同。
④“本主”是白族信仰的民间宗教,包括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本主庙。
⑤“张灿兴”是身份证上用的字,但他本人更喜欢用“张璨鑫”这三个字,认为似乎这样看起来更具有文化意义。
⑥在山上收割草料,喂养牲畜。
⑦无论写景、写人、叙事抒情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中间无夹的一唱就是一本,故称为本子曲。
⑧阿吒力:梵文音译,原意指能够为人传法、灌顶的密宗上师。此处为白族佛教密宗。南诏时期受到印度密宗影响,与白族文化融合后形成。
⑨阿央白:白语,女性生殖器之意。男女夫妇为求子嗣要来此跪拜。跪拜时要将香油等抹在阿央白上,以求顺产。
⑩由于老乡对于以一年来统计他们的现金收入这种形式不是很熟悉,故此数据可能不是很准确,但可提供一个大致的参考。——笔者注
参考文献:
[1][元]李京.云南志略[M]//明·陶宗儀.説郛.李际期宛委山堂,刻本.清順治三年(1646).
[2]张明曾.一个白族村落的文化变迁[C]//白族学学会.白族学研究.1994.
[3]罗明辉.关于洞经音乐问题的探讨[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4).
[4]伍国栋.白族音乐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185.
[5]张文,陈瑞鸿.石宝山传统白曲集锦[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3.
[6]杨延福.剑川石宝山考释[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15-16.
[7]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262.
[8]张文.白族歌谣发祥地剑川石宝山歌会[C]//唱响白族歌谣,我们踏歌而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267.
[9](日)板恒俊一.中国云南省白族调歌文化[C]//唱响白族歌谣,我们踏歌而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79.
[10]张文,羊雪芳.白乡奇葩——剑川民间传统文化探索[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117.
[11]杨曦帆.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白族音乐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