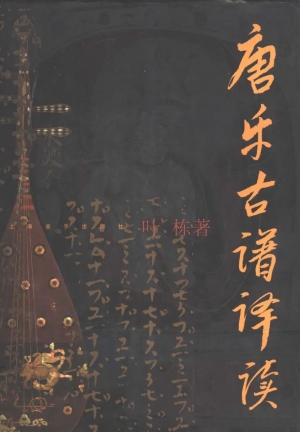叶栋先生自1963年开始侧重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为编写教材他开始深入各地对民间器乐音乐进行记谱整理、分析研究,1965年前后受西安鼓乐、林谦三《东亚乐器考》等方面的影响,开始关注敦煌曲谱研究。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输出,叶栋先生于1981年前后撰写的《敦煌曲谱研究》,一经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并继而拟定了12个相关古谱解译研究的课题。
该书集结了叶栋先生1982-1989年发表的相关系列研究成果,包括论文(10篇)和译谱(142首)两大部分,1990年代,由叶栋遗作整理小组历时七年整理编订而成。
序一
钱仁康
我国唐代的音乐在作曲和演奏技巧方面都有高度的发展。可惜唐乐到了宋朝就几乎全部失传,残存的曲谱也无人能够认识了。从宋朝到现在,听不到唐乐的声音,已经一千多年了。
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篆在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清除石窟甬道的积沙时,发现一间石室里藏着从晋到宋近十个朝代的各种写本和文物数万件。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把敦煌石室的九千件左右宝贵文物劫运至伦敦;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又把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劫运至巴黎。现藏巴黎图书馆的敦煌写本中,有一卷曲谱是五代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抄写的唐曲。目前所知,这是仅存的一套唐代曲谱。从30年代起,许多中外学者对这套曲谱进行了研究,但直到80年代初,还没有人能够把曲谱中的谱字、符号和文字标记解释清楚,因而也就不能真正解读这套曲谱。
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教授叶栋,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工作,为了使唐乐重闻于今,他决心解译《敦煌曲谱》。在我国前辈学者任二北、潘怀素诸先生和日本学者林谦三氏研究敦煌曲谱的基础上,根据我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参证有关典籍,对前人的研究舍短取长,去芜存菁,肯定了林谦三氏认为《敦煌曲谱》是琵琶谱和二十五曲分三组定弦的见解,肯定了任二北先生“唐俗歌绝非一句一拍”,“《西江月》辞每片四句、四韵”,和对板眼符号的见解。这三组琵琶曲到底如何定弦,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叶栋认为这些琵琶曲是载歌载舞的大曲,他根据女声便于歌唱的音域,并从福建南曲琵琶和日本琵琶风香调的定弦得到启发,确定了三组乐曲的三种定弦方法及其与调式调性的关系。于是谱字的解读,得以迎刃而解。对于节拍符号,也根据传统音乐的特点,参证宋张炎《词源》、王灼《碧鸡漫志》有关唐大曲节拍的论述,作了合理解释。经过刻苦钻研,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把二十五曲全部解译成功。
敦煌曲谱的解译,使我国古老的艺术珍品重放光芒,使绝响已久的唐乐重闻于今,从而填补了音乐史上的一个空白点。从译谱来看,唐代乐曲并非五声音阶,而是七声音阶的音乐,有时还有丰富的半音变化,它们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节拍体系和调式体系,并有一整套相当完整的记谱法。从而可以看到,我国音乐文化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敦煌曲谱的解译,不仅有利于发扬古代音乐文化,同时对古代社会、历史和文艺的研究,也有重大意义。许多描写唐代乐舞的文艺作品,将因敦煌曲谱的解译而得到新的理解。
叶栋曾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下,仍念念不忘敦煌曲谱的研究。“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党的文艺政策得到了落实叶栋扩大眼界,打开思路,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加速了敦煌曲谱解译成功的步伐。
完成对《敦煌曲谱》的解译后,叶栋又对《五弦琵琶谱》、《仁智要录》筝谱、《三五要录》琵琶谱、《博雅笛谱》等古谱进行研究和解译,并陆续在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这些成果对于中国音乐史,特别是唐代音乐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叶栋从事民族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对古谱的研究,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国之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拼了命去干的。他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叶栋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这种研究的。前人之功不可没,但是真正能够拿出成果来的,在中国,叶栋教授是第一人。他把《敦煌曲谱》等古谱翻译出来在国内是最早的,而且可以说,后来的人的研究都是由他带动的,他是开了风气之先的人。他在正当年轻有为、可以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就不幸去世了,这是非常令人痛惜的。所以我们应该纪念他,把他花了很大心血的遗作搜集整理出版;并遵从他的遗愿,努力完成他的未竟的事业。
钱仁康
2000年3月10日
叶栋先生1957-1963年在钱仁康先生领导的音乐理论教研室担任理论作曲系助教工作
图为他与钱先生(左)交谈唐古乐谱的研究(殷立民摄)
序二
江明惇
四十多年前,我在作曲系本科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刚毕业留校的学长做我们的助教。每当钱仁康教授上“作品分析”课之前,他先到课堂把批改好的习题本发给大家,上课时他和大家一样地认真听讲,课后又把大家的习题本收齐,看了提出意见,交给钱老师。大概因为不太熟,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此人很严肃,不苟言笑,后来才知道名叫叶栋。50年代末,我们去浙江收集《浙江吹打》,记好谱后,找他请教。他谦虚地说:“西洋音乐的曲式分析方法如何应用到中国器乐曲上来,是个新问题,我还研究不够。有共同的规律,又有不同的特征,不能用西洋曲式来硬套。”但从他的谈话中,我感到,他己经对一些著名的民族器乐曲作过分析,而且很有见地。60年代初,学校为了加强民族音乐教学和研究,建立了民族音乐作曲系和民族音乐理论系,叶栋从作曲系调来从事民族器乐的研究,我们开始在同一个教研组里工作。他一头钻进了资料堆里,大约过了半年多时间,他告诉我,已经把学校图书馆、唱片室、资料室里所能见到的中国民族器乐曲资料,全都分析了一遍,还拿出一大包卡片来。一曲一卡,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我当时感到,在他身上有一股顽强钻研精神,工作细致、严谨,一丝不苟。不久,他又去北京和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搜集民间器乐曲资料。
他本来就很不好的身体,经过“文革”的冲击,更加虚弱了。但工作的劲头比以前更大了。他又钻进图书馆、资料室,对开放初期所看到的每一点新的信息都注意吸取,对每一个新的民乐作品和有关资料都不放过。70年代末,为学生开出了《民族器乐曲分析》、《世界的音乐》、《论文写作》等新课;出版了专著《民族器乐的体裁与形式》。有一天,他到我家里聊天,告诉我说,他在搞《敦煌曲谱》的解译,已经很有眉目了。他详细论述了关于乐谱、背景、论据,以及前人的有关成果和自己的观点。我们谈得非常兴奋。这在当时是音乐学界、史学界都还无人敢于问津的领域。这个成果将会把中国音乐史的音乐实体向前推进一千多年,并打破中国音乐史被喻为“哑巴音乐史”的沉寂局面。是个了不起的成果。记得那天我们谈得很多,他还说到,敦煌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和骄傲,但被西方人掳掠去了,以至今天有人说“当今敦煌研究的中心在巴黎”。他是怀着这样一种民族责任心、民族自尊心来发奋研究的。后来他先在民族音乐理论教研组里谈了他的学术见解,不久在山东的 “民族音乐学研讨会”和上音学报《音乐艺术》上首次正式宣讲、发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82年,他应邀到西安、甘肃讲学,并且准备到敦煌看一看。谁料到了兰州就因为身体太虚弱,不适高原气候而病倒。幸得甘肃人民医院的及时抢救,护送回沪。以后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他的身体,他自己则说:“别的没什么,就是我的计划还没完成,我肚子里还有些东西要留下来。”几次病危抢救,我赶到医院看他时,他都是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他是在和生命争夺时间。在严重的病魔折磨和有限的条件下,他凭着顽强的意志、科学的安排,在十多平方的书房里艰难地、一步一步地挣扎着前进。终于完成了对《五弦琵琶谱》、《仁智要录》(筝谱)、《三五要录》(琵琶谱)和《博雅笛谱》等的解译和一系列论文的撰述。
日月如梭。一转眼,叶栋离我们而去已经十一年了。但我一直在怀念他。十一年以来,我国的音乐学、音乐史学都有很大的发展。就古谱的解译方面来讲,也有很多新的成果出现。但叶栋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领先打破古谱解译领域的沉寂,其先导作用和学术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叶栋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功绩,不是偶然的。我以为至少有这样三点值得我们牢记:一是对于事业的献身和勤奋精神;二是崇高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三是不因循守旧,不墨守陈规,善于学习而又不迷信“权威”。
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整理出版他的唐乐古谱解译方面的主要论著和译谱,供后来者学习,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钟英同志和金建民、王汝源同志,以及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同志们为此作出了努力,也是很有意义的。钟英同志嘱我写序,只是记录以上一些回忆,以寄托思念之情。
江明惇
2000年9月24日
1963年,叶栋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发展民族音乐的号召,转而重点研究民族音乐,是年他到西安调查研究陕西鼓乐,访问民间艺人,收集资料。
作者简介
①钱仁康(1914-2013),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博士生导师,历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音乐学系主任。出版著作:《音乐作品分析教程》、《外国音乐欣赏》和《欧洲音乐简史》等数十部;创作歌剧《江村三拍》和《大地之歌》。
②江明惇(1938-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主要著述:《汉族民歌概论》、《中国民族音乐欣赏》、《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上海卷》、《试论江南民歌的地方色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