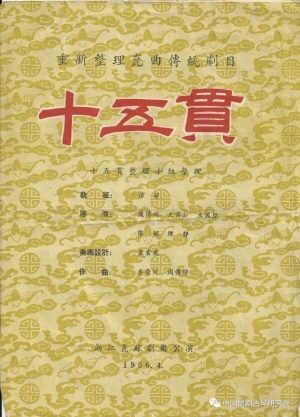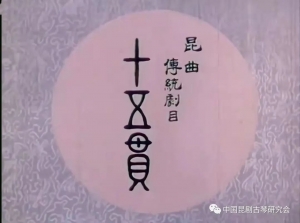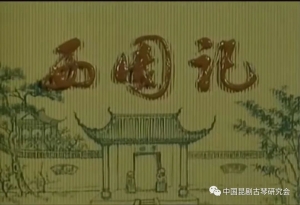摘 要:1956年,由浙江省昆剧团改编的昆曲《十五贯》在北京上演后大放异彩,周恩来总理观看演出后称赞《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浙江省昆剧团趁热打铁将传统舞台上的昆曲表演进行再次加工整理搬上荧幕,成就了昆曲电影史上最成功的典范之作,即昆曲电影《十五贯》。昆曲和电影之间融合形成了昆曲电影所独有的意境,昆曲电影也使昆曲的传播范围变得更广。昆曲电影《十五贯》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对当下发展呈弱势的昆曲电影乃至戏曲电影的传播和发展都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一、绪论
1905年,由“伶界大王”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问世,《定军山》不仅是我国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我国第一部戏曲电影。因为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也因为观众的接受程度不同,电影这种“洋艺术”进入中国之初,在很大程度依赖了中国的传统艺术——戏曲。
1931年,我国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中,穿插了京剧《穆柯寨》《玉堂春》《四郎探母》《拿高登》四出戏的唱段,观众从陌生的电影银幕上第一次听到了熟悉的传统戏曲唱段,中国电影也由此发出了如婴儿般的第一声嘹亮的“啼声”。
1948年,著名导演费穆和我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合作,将京剧《生死恨》搬上了电影荧幕,成就了我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的诞生。
由此可见,早期的电影发展和戏曲是密不可分的。传统戏曲是中国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在旧时中国人民的文艺生活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因此电影初次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之时,在不被中国人民认同和接受的环境下,需要借助传统戏曲的力量,来帮助自身成长。以电影为手段、形式,以传统戏曲为内容,让观众们熟悉、接受、喜爱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20世纪50至80年代,戏曲电影整体处于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戏曲种类高达三百六十余种之多。其中,昆曲作为“百戏之祖”,以其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而被称作戏曲百花园之中的一朵“兰花”。在戏曲电影的整体繁荣阶段,相比京剧电影、越剧电影等戏曲电影种类,昆曲电影的发展略显低迷。1920年,由梅兰芳大师主演的《春香闹学》可能是第一部昆曲电影,但无奈《春香闹学》影像资料毁于战火,早已无从考证。在此之后,陆陆续续拍摄的昆曲电影因为受众少,市场小,数量也相对较少,昆曲电影也未曾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
直至1956年,昆曲电影的发展获得了新生。由浙江昆苏剧团排演的昆曲电影《十五贯》问世,这部“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好戏被搬上了电影荧幕之后,使昆曲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二、昆曲电影《十五贯》产生的背景
(一)戏曲《十五贯》的诞生与进京演出
浙江省昆剧团成立于1955年,是在原民间戏班“国风苏昆剧团”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昆剧表演团体。1955年,剧团排演了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剧《十五贯》。时任上海市电影局局长的张骏祥和浙江省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的黄源观看完国风苏昆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后赞不绝口,并将改编后的演出剧本送给了当时我国文艺界和戏曲界的一些专家,专家们看过剧本后对《十五贯》的认可度也很高,当时这出戏在行业内部引起了一次小范围的轰动。
1956年初,国风苏昆剧团来到上海演出《十五贯》,上海市的文化界领导在观看完演出之后决定将《十五贯》送到北京演出。浙江省文化局还决定将“国风苏昆剧团”转型为国营演出团体,改名为浙江省昆剧团。
同年4月8日,浙江省昆剧团在北京市前门外的广和剧场第一次演出了《十五贯》,许多北京文艺界的名人前来观看演出,田汉、梅兰芳、欧阳予倩等文艺界的大家也在观众席当中。时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的田汉观看完演出回到家后连夜写成《看昆苏剧团的〈十五贯〉》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要求北京戏剧界以及话剧界的同志们具体地学习他们整理、继承遗产方面的“先进经验”,随即北京文艺圈中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4月17日,剧团应邀进中南海为毛主席等领导人演出。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出差回京后更是亲自来到广和剧场观看演出,浙江省昆剧团与《十五贯》一时之间成了我国文艺界独一无二的热门话题和焦点。文化部和中国剧协专门以《十五贯》为优秀文艺作品的范例,召开了大型座谈会,周恩来亲自出席会议,并作出指导性、总结性的讲话。次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讲话,发表了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
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
在《十五贯》轰动效应的推动下,北京、江苏、上海等地相继恢复或建立昆剧表演团体。昆曲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被重新认识。昆曲《十五贯》的整理改编取得成功,一改昆曲艺术濒于衰亡与湮没的境地,使其走上改革与复苏之路。《十五贯》的成功,创造了“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奇迹,成了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十五贯》的主演,况钟的扮演者周传瑛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当时周总理在后台与剧团演员们的谈话时回忆道:“总理首先就鼓励了我们,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
(二)原唱段改编和传统戏曲改编的借鉴之处
《十五贯》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对原故事和原唱段的改编。戏曲《十五贯》最初是由清代戏曲作家朱素臣根据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第三十三卷《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改编而成的,而《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故事又是从宋元话本《错斩崔宁》演化而来的,又名《双熊梦》。
原本的《十五贯》故事主角为双生双旦,别名《双熊传》中的“双熊”指的是熊氏兄弟二人,二人有各自的两条情节线索,本来是两个独立又相互交织的“十五贯”故事,讲的是熊友兰、熊友蕙两兄弟因“鼠”致祸含冤,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的况钟为两兄弟平冤昭雪的故事。全本的原作共26出,搬上舞台需演12个小时,至少要连续演出两三个晚上,不仅剧团演员疲劳,也难以保证如此之长的剧目能吸引观众。综合考虑后,浙江昆苏剧团将其删减为八出,将“双熊”的故事缩减成“单熊”的故事,形成了长度为3个小时的全新版本。
在《十五贯》改编之前,毛泽东主席在肃反运动中强调了提高警惕、防止偏差的方针,还专门为此批发了《胭脂》《席方平》等有关指导正确办案处理冤情的材料。主席更是强调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基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剧团编剧将剧本原来“批判昏官,颂扬清官”的主题上升为“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和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十五贯》贬斥了县官过于执武断执拗、脱离实际、妄断人命的官僚作风,颂扬况钟为民请命、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为官风格,正切合当时毛主席所倡导的“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用参与改编的黄源局长的话说,就是“把过于执和况钟两种审案的态度,提高到主观主义和实事求是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
《十五贯》的成功改编为我们改编传统戏曲剧目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一是压缩原本过长的剧目,从中选择有看点、戏剧冲突明显的故事情节,和具有典型特征的主要人物。如改编后的《十五贯》删掉了熊友蕙的故事线,即使只留下单生单旦的故事线索,也足以烘托主人公况钟的正面人物形象,适当地缩减人物数量,也使得留下的人物形象更能重点突出,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性格有了更直接的理解。再如剧中重点描绘了“案件起因”“况钟断案”“庙中捉鼠”三部分的情节,使况钟实事求是、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为官风格更加一目了然,故事的主题更加鲜明。
二是艺术创作和改编都需要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真正做到“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现今的艺术创作也应该像《十五贯》学习,把握主流价值观、结合时代背景,这样才能做到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的要求。
重新整理昆曲传统剧目《十五贯》剧本书影
(三)拍摄昆曲电影《十五贯》
为满足全国各地观众都想观看《十五贯》的需求,也为了继续扩大《十五贯》的影响。浙江昆苏剧团圆满结束赴京演出后便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昆曲电影《十五贯》,并采用舞台版原班演员,由有着多部戏曲电影拍摄经验的陶金任导演。舞台版的《十五贯》经过改编后,压缩成了三小时十五分钟的版本,要把这出戏搬上电影荧幕,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需要再次缩减时长。陶金导演和摄制组的工作人员,确定了四项原则作为压缩剧本的中心环节。第一,必须突出强烈的主题思想;第二,保持人物性格的鲜明;第三,要使故事情节清楚完整;第四,不能削弱舞台上精彩的表演。遵循着这四点原则,导演和编剧又征求了剧组老戏曲演员的意见,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将剧目缩短至一小时五十五分钟。导演陶金在他的拍摄杂记中提到“戏曲有戏曲的特性,电影有电影的特性,戏曲影片是把两个特性恰当的结合的问题,结合的好,就应该比原来的更完美,更丰富”。
三、视听浅析:昆曲电影《十五贯》中戏曲元素和电影元素的运用
作为昆曲电影来讲,《十五贯》是较为成功的,并且在戏曲电影史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正如陶金导演讲的那样,《十五贯》将戏曲和电影的两个特性恰当地结合在了一起。
相较于在戏曲电影中占比重较大的京剧电影,拍摄昆曲电影更为复杂。研究昆曲电影,先从昆曲说起。首先,就昆曲本身而言,昆曲不同于京剧的板腔体,而是曲牌联套体。所谓曲牌,其实就是昆曲曲调的调名,就像一个人的名字一样,曲调也要有名字,如“皂罗袍”“山坡羊”“懒画眉”等。曲牌,由词发展而来,每一支曲牌都有自己的风格。昆曲电影《十五贯》为保证原汁原味,也尽量完整地保留了每一支曲牌,使电影版本也不失昆曲的韵味。每一支曲牌又都根据剧情的要求,把曲调加工或变化。例如:在电影中,虽然沿用了《山坡羊》《泣歌回》《石榴花》等原戏曲中的曲牌,但除了开始和结尾的地方仍用原谱外, 中间部分都根据内容和字韵的不同做出了全新的加工处理。剧中况钟在“判斩”一折中的《混江龙》《天下乐》的曲牌使用,都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时况钟内心的挣扎和纠结,极大地帮助演员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使观影者能更好地了解角色的人物性格。再例如“访鼠”一折的打击乐应用,在紧张的《急急风》节奏中,加入了灵动流畅的《水底鱼》,恰到好处配合了破案的经过,彰显出了况钟的机智巧妙。电影《十五贯》中曲牌的应用,与演员的内心反应是一致的,可以理解为是“内心戏”的另一种表现手法,也是一种用来帮助刻画人物性格不可或缺的手段。
电影用最常见的叙事手法——正叙,从头开始讲起,将故事娓娓道来。本影片同其他许多戏曲电影一样,采用全知视角讲述故事,即站在第三人的角度,像“上帝的眼睛”一般无所不知地向观众传达信息。这种叙事角度对于后面故事的发展,即案情的侦破,起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昆曲电影《十五贯》片头
影片的开端先用大全景空镜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一个江南小镇的夜晚,这里尤其应该注意一下小镇里“桥”的出现,尤葫芦外出归家经过了这座桥,后面苏戊娟逃跑时也经过了这座桥,此处体现了电影布景的巧妙之处,更能营造观众的“上帝视角”。苏戊娟误信了继父尤葫芦的玩笑说要将她卖到员外家,“投亲莫迟延”逃跑出家时,导演还巧妙地运用了一个长镜头,交代苏戌娟跌跌撞撞逃出家门,因为惊慌并没有将家门锁好,等苏戊娟经过小桥跑远之后,长镜头中才出现了娄阿鼠偷偷摸摸的身影,他正好看到了苏戊娟逃出家门,并且家门没有上锁,才引发了后面娄阿鼠杀人偷钱的案件。
影片中为烘托人物心情所使用的正反打镜头也十分考究。如尤葫芦戏弄苏戌娟说将她卖到王员外家做丫环时,父女两人的正反打镜头剪辑。尤葫芦对女儿说:“王员外家缺少一个丫头,我收下他十五贯钱,将你卖了”,在说“卖”字的时候,父亲故作哭腔,“卖”字说得断断续续,在念白的气口处,由尤葫芦的画面切为苏戌娟紧锁眉头的中景,形成正反打镜头,之后又切回尤葫芦的镜头,在最后“了”的重音处,又切为女儿的中景,拍到女儿脸上的惊恐和悲戚。如此烘托人物心情的正反打镜头还用在了电影最精彩的情节“测字”中。况钟假扮算命先生为侦破案件到寺庙中给娄阿鼠测字,引他上钩自己交代出犯案过程。娄阿鼠求测字先生指点迷津时,两人的正反打镜头,突出了娄阿鼠当时的慌张,也交代况钟布下圈套使娄阿鼠一步步上钩的故事情节,烘托了情节的紧张氛围,推动着故事向下发展。
戏曲电影的一个妙处就是可以运用电影的艺术手法放大戏曲故事的细节之处。例如娄阿鼠杀死尤葫芦,偷盗十五贯时,因为做贼心虚怕人发现,匆忙之间扯断了串着十五贯的线绳,不得已跳上床收拾铜钱,后面况钟来到案发现场复查此案时,在床边发现了娄阿鼠独有特制的骰子,铜钱散落的特写镜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破案的关键。
《十五贯》中镜头和蒙太奇的配合应用也十分巧妙。影片中况钟初次在堂上审案时,影片中采用了平行蒙太奇的手法来表现:苏、熊二人来到苏州巡抚处等待斩首,况钟发现案子有疑点,于是派童儿前去悦来客栈找老板来核实。一边是苏州巡抚在公堂之上仔细查看案宗寻找漏洞,一边是书童夜晚提灯前去悦来客栈。这种电影中常用的平行蒙太奇表现手法,戏曲舞台上却没有办法呈现,一般的舞台演出都会省去这个情节。再如后面况钟在堂审苏、熊二人,认为两人有冤情之后,连夜求见都察院御史周忱,在府衙内焦急等待周忱,此处越燃越短的蜡烛、谯楼上的钟响和况钟在府衙内来回踱步,三者交替剪辑表现出况钟等待了很久周忱才不情不愿地升堂,配合况钟的念白“急在心间,坐立不安,刀下留人,时光本有限”,表明了况钟为民请命的焦急和周忱的官僚架子与略显昏庸的特点。两官的性格不同,更能凸显况钟的为官正直、为民请命,不愧为熊友兰唱段里所讲的那样“如包公再世”。
昆曲电影《十五贯》 周传瑛 饰 况钟
电影版本《十五贯》的叙事速度和舞台演出版也是不一样的,电影中的表演比舞台上的速度要更快。在舞台上念白要遵从戏曲的传统艺术形式,适当拖慢,拉长唱段,从慢节奏中让观者细细体会戏曲艺术的意蕴。而经过电影的处理,镜头与拍摄对象之间的空间转换便显得自由了,演员唱、念的速度变为电影的速度,在原有的表演形式和韵味的基础上适当的加快,使观众觉得快慢合适,减轻了戏曲艺术原有的缓慢沉闷之感。陶金导演在处理电影节奏方面总结了经验:“同一个戏,作为戏曲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表现,剧情人物内在总的节奏尽管相同,但舞台上和银幕中的表现是有着差别的;并且电影的蒙太奇比起戏曲的舞台调度,在推动节奏的变化上比较灵活便利,因为一个是舞台整体的运动,一个是镜头的变化,后者的时间需要是较为经济的。”
四、昆曲电影的传播与发展
戏曲版本的《十五贯》因为各种条件所限,并不能使全国各地区的观众欣赏这出戏的魅力所在。而昆曲电影《十五贯》则可以满足更多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也为电影本身扩大了社会影响。南京大学的傅谨在《昆曲〈十五贯〉新论》中评论:“准确完整地评价《十五贯》的历史地位,除了要看到它在政治领域被用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工具这一其实并无多少实际价值的所谓‘教育意义’,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在戏剧界所产生的非常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十五贯》不仅仅在传统戏剧改编方面具有示范意义,从传统剧目如何获得当代的角度看,它的贡献更是无与伦比 。”
(一)昆曲电影在当下的发展:昆曲电影和昆曲化电影
昆曲电影的整体数量不多,《十五贯》可谓是其中的经典之作,更是昆曲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十五贯》大获成功之后,昆曲电影也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1960年梅兰芳先生主演了昆曲电影《游园惊梦》;1964年出品了由俞振飞主演的昆曲电影《墙头马上》;1979年执导过《十五贯》的陶金导演还执导了昆曲电影《西园记》,这几部也同样是昆曲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但从1995年以后,昆曲电影的拍摄就进入了一个低谷。但其中有一个独特的类型:昆曲化电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昆曲电影《西园记》
其中知名度最高的、观众们最熟悉的是2001年杨凡导演执导的电影《游园惊梦》,这部电影由王祖贤和日本演员宫泽理惠主演,故事讲述了两位女性之间的感情故事。故事的背景选在了民国时代南方的一户深宅大院中,昆曲跟这样的故事背景十分贴合。我国南方特有的假山园林和昆曲悠扬曲调交相辉映,“游园惊梦”“长生殿”“夜奔”等唱段轮番登场,烘托着主人公在不同剧情中不一样的心境。
其实昆曲化的电影和单一的昆曲电影相比,更有利于昆曲的传播,更能让不太了解昆曲、戏曲的人,理解唱段,了解戏曲艺术。
再如1963年的电影《桃花扇》,也可以称之为昆曲化的电影,它的主演都是有昆曲舞台表演经验的演员,影片中也选用了很多昆歌、昆曲的片段,使影片整体的艺术层次得到了一个提升,同时也使观众们了解了昆曲的独特韵味。
(二)昆曲电影的未来之路
近年来昆曲电影做了许多新的不同尝试。
2018年,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出品、上海昆剧团创作演出的首部中国3D昆曲电影《景阳钟》在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得了金鹤“艺术贡献奖”。影片将原本两个多小时的舞台演出版压缩成了100分钟的电影版。改编时,对原本剧中起情节铺陈作用的第一场“廷议”、第二场“夜披”等折子进行删减,使故事情节更为紧凑突出、足够吸引观众。同时3D的电影技术也增强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电影开场便是万马奔腾的大景别,展现出了3D特效,凸显了前方战事吃紧的故事背景。为了进一步增强画面视觉冲击力,突出“3D”这一独特的形式,上海昆剧团特别对“乱箭”一折中的武戏场面进行新的加工,在强化戏曲表演程式的同时,使开打场面更震撼人心。由此可见,昆曲电影相比于舞台版的昆曲,确实能在大场面布景上使观众有更强的代入感。
再如,2015年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出的3D昆曲动画片《粉墨宝贝》,讲述的是两个卡通小主角在“小昆班”学习昆曲的故事,这是传统昆曲与现代动漫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第一次“跨界合作”的作品。《粉墨宝贝》克服了跨界艺术合作上的种种问题,以及3D动画制作的诸多技术难题。在数十位昆曲表演艺术家的全程指导下,《粉墨宝贝》巧妙地在动画片中融入传统戏曲文化,让少儿观众们从小便接触昆曲艺术,这也是昆曲和昆曲传播的一种新尝试。
昆曲动画片《粉墨宝贝》
昆曲电影如何更好地发展下去,如何走一条更长的发展之路,这确实还需要不断地尝试和摸索,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探究的议题。电影和戏曲(昆曲)之间的矛盾尚没有更好地化解开来,这两种艺术的表现手法差别巨大,“电影+戏曲(昆曲)”并没有达到1+1>2 的艺术效果。但是昆曲和电影之间依然融合出了昆曲电影所独有的意境,昆曲电影也使昆曲的传播范围变得更广,让更多的观众欣赏到了昆曲。相信作为“新兴艺术”的电影在未来还是能够从昆曲这一传统却历久弥新的艺术形式中吸收到新养分,成长得更加茁壮,同时帮助昆曲艺术传播得更远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