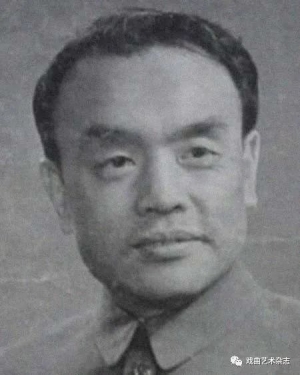摘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中,形成了以“北刘(吉典)南于(会泳)”为代表的作曲家群体。本文主要以《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为例,分析刘吉典在音乐创作中所遵循的新音调、新形式、新手法等原则,探讨于会泳如何通过唱腔音乐设计的广度和深度、正确发挥器乐的表现功能实现塑造人物音乐形象的根本任务。两个创作群体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和交融,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音乐创作观念和技法,形成了这一时期现代戏音乐创作的巨大成就。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与于会泳相比,戏曲音乐界对刘吉典的研究尚显不足。如何完整地继承“北刘南于”为代表的戏曲音乐成就,开拓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观念,推动京剧现代戏的全面发展,仍是当下戏曲界应重视的课题。
关键词:刘吉典 于会泳 南北互动 创作观念 作曲技法
戏曲现代戏创作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本文试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北两地音乐家之间的交流互鉴为切入点,探讨早期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是如何推动起来的,都形成了哪些创作观念和作曲技法,这对于戏曲现代戏音乐创作,乃至对今天戏曲音乐的整体创作有哪些启发意义。
一 、南北两地:新老音乐家结成的创作集体
这里所说的南北两大京剧音乐创作群体,指的是北京以刘吉典为代表、上海以于会泳为代表的音乐家群体。
以刘吉典为代表的创作群体,主要包括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两个创作集体,主要有:刘吉典、李少春、李金泉、张建民、戴宏威、李慕良、张君秋、陆松龄,等等。
以于会泳为代表的创作群体,多为参与上海京剧院几部现代戏音乐创作的骨干,主要有:于会泳、刘如曾、黄钧、沈利群、陈立中、高一鸣、庄德淳、龚国泰、军驰,等等。
这两个音乐创作群体分别在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和上海京剧院的创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既相对独立,又有相互影响、启发和交融,比如,李慕良曾参与《智取威虎山》的修改,于会泳也曾参与《红灯记》的修改。
本文主要以《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创作为例,因为这两部戏是最早完成电影拍摄的“样板戏”,它对之后拍摄完成的《沙家浜》《海港》《龙江颂》《奇袭白虎团》《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磐石湾》等多部京剧现代戏的创作、修改和定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 、刘吉典:探求新音调、新形式、新手法
刘吉典先生是探索并实践戏曲音乐现代化的先驱之一。他1953年随作曲家马可先生进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戏曲音乐研究工作。1955年调入中国京剧院任艺术室音乐组组长。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京剧现代戏《白毛女》(1958年创作)的作曲家之一。随后,他同一批艺术家一道投入到京剧《红灯记》的创作之中。

刘吉典
为了更好地反映新题材、新内容、新人物,在创作之初,他们就提出了在音乐创作上必须与之相适应地“探求新音调、新形式、新手法”。正是遵循了这条创作原则,音乐家们为塑造好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大胆创造了新的音乐程式和音乐语言。
1.关于新音调
在唱腔设计上能否摆脱传统京剧音调在表现新人物时的陈旧感,而使人物的音乐语言更富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是唱腔设计中的关键问题。刘吉典在创作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只有对新的人物性格、气质和他们的语言、神态准确地把握,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在构思人物的唱腔时就有可能把其新的语言音调生动地反映出来[1]。《红灯记》中铁梅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就是由刘吉典先生提议并设计完成的,由此成就了一段家喻户晓的新颖唱段。李铁梅“我家的表叔数不清”那种渗透在唱腔中的小姑娘猜大人心事的活泼、得意的语态,通过唱腔把铁梅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一段完全突破传统【西皮流水】的音调和格局,板后起唱,2/4、1/4、3/4节拍并用,更赋予唱腔旋律和节奏少见的或整或散、时疏时密的活泼形态[2]。剧中李奶奶“说家史”中唱到“说明了,真情话,铁梅呀,你不要哭……”好像生活中老人亲切地呼唤晚辈的音调,也是运用新音调的成功范例。同时,为避免京剧现代戏在运用程式化的声腔表现新人物时有隔世之感,在字韵和演唱方法特别是润腔方式上也进行了改革。
2.关于新形式
在京剧声腔中由于不同行当大、小嗓演唱方式的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演唱音区,不同行当特别是在【二黄】【反二黄】对唱或联唱时,音区难以统一,这一直是个技术难题。《红灯记》第五场李奶奶“闹工潮”后面紧接李铁梅唱段“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为了保持情绪和音乐的连贯性,以刘吉典为代表的音乐家巧妙地运用【二黄】与【反二黄】的转调方式,以1-5弦唱【二黄】腔,创造出了【反弦二黄】。这一新形式的运用,不仅很好地解决了两个行当在音域和常用音区上的矛盾,而且改变了传统旦角【二黄】腔的听觉形象,把此时此刻铁梅的意志和决心表达得特别充分。这种高拉低唱的【高调二黄】对《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旦角唱腔中高调【反二黄】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凡此种种,无论是唱腔布局的层次感和表达情感的准确性、深刻性,还是新的声腔和板式设计,都成为用一切手段完成塑造人物这一最高任务的新创造。
与此同时,音乐家们又不是一味地盲目求新求变,而是十分重视对传统的学习和运用,使得该剧的唱腔音乐创作成为了很好地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典范。如李玉和“雄心壮志冲云天”一段,从唱腔结构到旋律借鉴了传统戏《逍遥津》,但经过新的处理后,音乐形象发生了改变。这段充满人物丰富情感的成套唱段,既依托传统,又大胆革新,成为全剧最具感染力的核心唱段。
3.关于新手法
在现代戏的创作中除了唱腔以外,器乐曲也是塑造人物形象、渲染戏剧氛围、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手段。《红灯记》的创作中,全剧的幕间音乐、念白配乐、戏剧性的描写音乐,以及唱腔中的长过门,对丰富音乐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3]。该剧红灯音乐主题、李玉和人物主题的设计,以及《大刀进行曲》《国际歌》《东方红》等音调的运用,是主题音乐贯穿手法引入京剧音乐创作最初的探索和实践。这种“专曲专用”创作手法,改变了过去传统京剧“一曲多用”的做法。运用音乐主题在剧中贯穿发展,使之在表现情感的丰富性和渲染戏剧冲突的发展中,求得变化中的统一,是《红灯记》创作中一个显著的特征,为拓展京剧音乐创作手法做了成功的尝试。
三 、于会泳:戏曲音乐的根本任务是塑造人物音乐形象
于会泳是在1965年作为上海“戏改音乐小组”负责人参与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两部戏的修改时开始京剧音乐创作的,但他对民族音乐以及京剧音乐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却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时,于会泳虽还未进入京剧音乐的创作,但他对刚刚兴起的京剧现代戏创作十分关注,做了大量的研究笔记,并发表了《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的若干问题》和分析《红灯记》《沙家浜》音乐创作等几篇较为系统的研究文章。他提出“发展新的音乐程式是戏曲音乐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戏曲音乐发展的必要的经常性任务之一”[4]。正是在对这一时期京剧现代戏创作实践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并且在对其经验进行归纳和总结的过程中,他形成了自己关于戏曲音乐创作观念和创作技法的独特见解。
于会泳
于会泳从对《红灯记》《沙家浜》音乐创作的研究总结中得出了“通过着重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途径来积极参与革命英雄形象的塑造,是京剧音乐和一切戏曲音乐最主要的任务”的结论[5]。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他不仅提出了唱腔设计必须坚持广度与深度相结合的原则,而且还将这一创作观念带入到《智取威虎山》的修改之中。
1.关于唱腔音乐设计的广度
在音乐布局上要有全局观念,从人物出发,根据主题思想、情节结构,按照各个人物不同戏剧情境下的舞台动作和内心世界,安排唱腔布局,以不同的声腔板式展现人物的多个侧面,多角度地予以完整的刻画。同时,经过通盘考虑,确定唱段的主次关系,保证音乐形象的完整性、连贯性,而不是像有些老戏那样“打补丁”“见缝插针”,杂乱无章。
要突出重点,在所有唱腔中突出主要唱段,在主要唱段中突出核心唱段,如杨子荣全剧有十二个唱段,其中“管教山河换新装”“共产党员”“迎来春色换人间”“胸有朝阳”是该剧的重点唱段,而又以“胸有朝阳”作为有层次的成套的核心唱段。
要实现上述两点有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作曲和编剧必须共同进行文学构思和音乐构思[6]。这一理念贯穿在了《智取威虎山》不断的修改过程之中。
2.关于唱腔音乐设计的深度
在旋律创作上要做到“三对头”,即感情、性格、时代感都对头。有时喜怒哀乐的情绪对头了,不一定性格对头;性格对头了,不一定时代气息对头。塑造英雄人物音乐形象,一定要使三者联系起来[7]。《智取威虎山》中“共产党员”“迎来春色换人间”“胸有朝阳”等几段唱腔都很好地把三者结合起来了。
在当年《智取威虎山》剧组的总结文章中还提出“继承和借鉴绝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必须“三打破”(打破行当、打破流派、打破旧格式)。在这样一些创作观念指导下,在唱腔、音乐写作时确实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但是,实际上该剧音乐创作上一些成果的取得,绝不是空中楼阁,许多地方恰恰都能找到传统的影子,如《打虎上山》杨子荣的“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被认为是革新力度最大的一段唱,其旋律却来自传统京剧《战太平》“头戴着紫金盔齐眉盖顶”。
以于会泳为代表的音乐家认为,吸收和化用革命歌曲的音调,并作为音乐主题在戏中加以贯穿运用,是实现深度塑造人物的有效手段,也是获得时代气息和新的气质的重要方法,如剧中《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音调的运用,都为增强时代感,塑造追剿队这一英雄群体发挥了有效作用。
与此同时,为主要人物设计具有个性的人物主题和下四度暂转调的特性音调,也在该剧中尝试性的得到运用。
人物主题:
杨子荣特性音调(谱例):
人物主题与特性音调的运用和贯穿,在之后几部京剧现代戏的音乐创作中,逐渐成为了重要的创作方法,尤其在《杜鹃山》的创作中这一手法运用得更加出色和自如[8]。
3.正确发挥器乐的表现功能
在现代戏创作演出中,随着乐队编制的扩大,正确处理器乐与声乐的关系成为了一个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从《智取威虎山》开始,样板戏的中西混编乐队的编制基本定型,由此,于会泳为代表的音乐家总结出了如下经验:伴奏部分要突出“三大件”,在西乐中以弦乐为基础。在器乐写法上切忌洋(缺乏民族特色)、怪(离奇古怪)、重(音响过强过厚)、杂(配器上复杂烦琐)[9]。
四、南北互动中形成的创作观念和作曲技法
在20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京剧现代戏创作的历程中,南北两地音乐家之间相互关注,从而在相互交流学习以及相互启发和借鉴中,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音乐创作观念和技法,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创作现象。观念是先导,技术是手段。整个现代戏创作时期在音乐创作方面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与这一时期南北两地音乐家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笔者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的戏曲音乐创作观念和作曲技法,大致归纳如下:
在创作观念上——
1.唱腔是塑造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段。
2.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3.重视唱腔与文学的关系。
4.关于演唱方法的改变。
在创作技法上——
1.采取吸收、嫁接等手法,创作新声腔、新板式。
2.主题贯穿手法的探索与运用。
3.探索中西混编乐队的编配技法。
余 论
刘吉典和于会泳都是20世纪不可多得的既有理论自觉又有实践经验的音乐家。刘吉典的京剧音乐创作实践要早于于会泳,《红灯记》《沙家浜》这两部北京创演的剧目深深影响着于会泳,这一点在他本人的文章中可以发现。同时,我有幸读到过于会泳的笔记,其中对此也多有记述。然而,与于会泳相比,对刘吉典的创作研究却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由于刘吉典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致使他过早地离开了创作一线,导致其在早期京剧现代戏创作中形成的创作观念和积累的经验无法延续,这是非常遗憾的。
这些年来,业内对于会泳的创作研究有所深入。我们发现从他参与创作或修改的《海港》《智取威虎山》《红灯记》《龙江颂》《磐石湾》,再到他基本独立完成的《杜鹃山》,其提出的主题贯穿手法、特性音调运用、唱腔布局原则以及中西混合乐队的定编和配器方法,这一整套系统的创作思路和方法,不仅在当年不少戏中有了实践成果,而且影响到当时京剧音乐的创作走向。
实际上,在京剧现代戏创作的早期,以刘吉典为代表的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的音乐创作集体,形成了与上海京剧院不同的创作风格和音乐追求,这种差异在《红灯记》《沙家浜》与《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的音乐创作风格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然而随着“样板戏”创作方法的模式化,北京变得越来越亦步亦趋,以至于北京京剧院《杜鹃山》的音乐创作完全由上海的团队来完成。如果当年以刘吉典和于会泳为代表的南北两地的音乐创作群体,能够按照各自不同的创作理念进行探索实践,或许会形成更加“百花齐放”的多元格局,甚至真正形成“双峰并置”的局面,就像话剧界的“北焦(菊隐)南黄(佐临)”一样。但历史没有如果,这不能不说是京剧现代戏创作中的一大遗憾。
(本文系作者根据在“戏曲现代戏舞台创作高端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文章有删节,原文见《戏曲艺术》2022年第2期。)
作者简介:尹晓东,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曲,作品有京剧《三寸金莲》《郑和下西洋》《知音》《青衣》《北平无战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戏曲作曲及戏曲理论研究。
注释:
1、刘吉典:《刘吉典戏曲音乐作品选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第4页。
2、汪人元:《百年诞辰,经典垂范——纪念著名戏曲作曲家刘吉典先生百年诞辰》,《中国戏剧》2019年第9期。
3、军驰:《现代京剧音乐创作经验介绍》(上),油印资料,1996年1月,第134页。
4、于会泳:《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上),《上海戏剧》1964年第6期。
5、于会泳:《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文汇报》1965年3月28日。
6、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满腔热情 千方百计——关于塑造英雄人物音乐形象的几点体会》,《红旗》1970年第2期。
7、同上。
8、参见军驰:《现代京剧音乐创作经验介绍》(上),油印资料,1996年1月第52-53页。
9、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满腔热情 千方百计——关于塑造英雄人物音乐形象的几点体会》,《红旗》197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