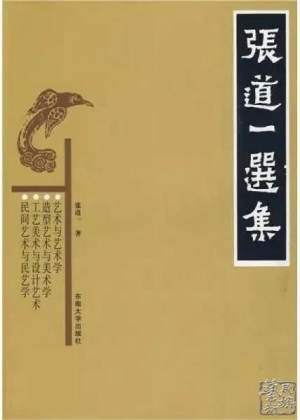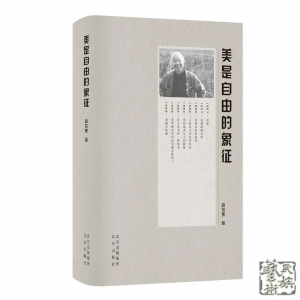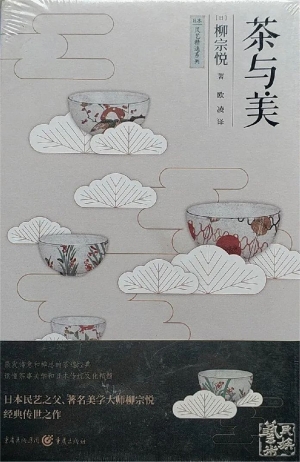摘要:艺术学由九个子学科组成,艺术原理开路,民间艺术学殿后,是为“抓两头带中间”。两个“头”一个是知识层面,另一个是存在层面。艺术原理是艺术学的基础,民间艺术是艺术的基础。美的艺术是“为艺术而艺术”,民间艺术是“为生活而艺术”;美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民间艺术的基本原则是自然。因此我们应当让民间艺术与美学脱钩。民间艺术让艺术从“美的艺术”或“天才的艺术”中获得突破,在事实层面延展了艺术学的广度;民间艺术学揭示了艺术在美和审美外的独立地位,在意义层面延展了艺术学的广度。民间艺术学还带来了艺术学的纵深,改变了对中国艺术史的理解,例如抵制将中国画窄化为文人画、突破“书画同源”的古老观念。“中国艺术学”要放在“艺术学的纵深”视域中加以理解。
关键词:民间艺术学;艺术学;张道一;文人画;艺术史
作者:郭勇健,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作者简介
郭勇健,文学博士(艺术学专业),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美学和艺术学理论。
2000年9月至2003年7月,笔者在东南大学艺术学系(现为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张道一先生。那几年,张先生已基本形成了他的艺术学学科体系构想,表达于《应当建立“艺术学”》《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艺术学的研究与方法》等一系列论文中。有一次在张先生家的书房里谈学术,他强调艺术学是对艺术进行综合性研究,主要由九个子学科组成,即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美学、艺术评论、艺术分类学、比较艺术学、艺术文献学、艺术教育学、民间艺术学。笔者问为什么要有这九个子学科?张先生说这是“抓两头带中间”。当时笔者认为艺术学这一学科以艺术原理为“头”是理所当然的,却从未想到民间艺术学也是另一个“头”,觉得张先生作为民间艺术研究的大家,或许不免对民间艺术学有所偏爱。然而时隔将近20年,回想张先生“抓两头带中间”之说,越来越觉得其中有深意在焉,越来越觉得民间艺术学对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本文便是在张先生思想的启发之下,初步探讨民间艺术学对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之意义。
《张道一选集》。这部文集收集了《应当建立“艺术学”》《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艺术学的研究与方法》等一系列论文,张道一先生的艺术学学科体系构想,在这些论文中初见端倪。
一、民间艺术学与艺术原理
艺术原理对于艺术学的头等重要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艺术学的子学科都是对艺术的某些方面的研究,而艺术原理是对艺术本身的研究。艺术原理甚至给出艺术的定义,给出区分艺术与非艺术的标准,就此而言,其他艺术学子学科都是建立在艺术原理之上的。如果我们将艺术学与此前的文艺学相比较,那么艺术原理与艺术史的关系,相当于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关系。杨春时指出:“文学理论是文艺学的基础学科,在文艺学中具有主导地位。文学史必须有文学理论的指导,才能提示文学的历史规律。文学理论可以解释文学的发生、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文学的思潮、流派、文学的历史演变等文学现象。如果没有文学理论的指导,文学史就可能变成文学资料的堆积。”艺术史家之所以能将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和汉代马王堆帛画纳入绘画史,都是由于有着艺术原理的“前理解”。
台湾艺术史家石守谦指出:“任何一部美术史的论述,不论作者是否有所意识,必定依循着某一个理论模式来作层层的开展。而这个理论模式又通常是环绕着‘艺术是什么’这种基本命题而建构起来的。”这是很有见地的。学术界也经常呼吁“以史带论”“论从史出”,但这只是意在提醒艺术理论应当与艺术史的实证材料相结合,不能“概念先行”,不能从概念到概念。尽管论离不开史,暗中统率和主导艺术史之实证材料的仍然是艺术原理。
正如“文学理论是文艺学的基础学科”,张先生显然也赞同“艺术原理是艺术学的基础学科”。实际上他把艺术原理与一般艺术理论做了区分。他主张艺术理论包括“技法性”理论、“创作性”理论和“原理性”理论三个层次;艺术原理就是原理性理论。原理性的艺术理论才可以视为“艺术学的基础学科”。但是,张先生提到民间艺术时,也经常使用“基础”一词。例如,“民间艺术是带有原发性的艺术,是大众的自发创造,因而构成民族文化的一个基础的层次”。“至于民间艺术,就其性质说,它是艺术的一个基础层次,也就是原始性的和原发性的艺术。一般不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也不与专业艺术并列。”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基础”的关系呢?换言之,该如何理解艺术学学科体系中“抓两头带中间”的关系呢?
一个事物可以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起源,这就是所谓的“多元起源论”,但从逻辑上说,一个事物不能有两个基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论事物的完整性时说:“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如果把张先生的说法改为在艺术学的九个子学科中,艺术原理是“头”,民间艺术学是“尾”,其他七个学科是“身”,似乎更加合乎逻辑。但张先生明明说的是“抓两头带中间”,而且对于民间艺术多次用了“基础”一词。怎么理解艺术原理是基础、民间艺术学也是基础呢?在笔者看来,这两个基础或两个“头”,分别指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或可视作知识层面与存在层面。艺术原理是艺术学的基础学科,民间艺术则是艺术这种文化形式的基础层面。艺术原理旨在确定艺术的概念、规定艺术的范围,因而主导了一切艺术学的研究,但与此同时,对民间艺术的关注与否,往往会影响或动摇艺术的概念。
民间艺术是自发性、原生性、基础性的艺术形态。它在时间上源远流长,在空间上无远弗届。如果说整个艺术是一座金字塔,那么民间艺术就构成了金字塔的底部。然而,以往的美学研究艺术,往往集中于上部,甚至聚焦于塔尖,也就是被看作经典艺术或高雅艺术的部分。金字塔的底部和尖顶是一种高低等级关系,因此,塔尖部分代表着高级艺术,塔基部分代表着低级艺术。此前美学聚焦于塔尖部分,大概是认定事物的本质要在事物发展的较高阶段才看得出。朱光潜曾指出:“文艺到现代大致已离开‘自然流露’而进到‘有意刻划’的阶段,这就是说,它已经变成有‘自意识’的活动了。”民间艺术显然是自然流露的艺术,尚未发展到拥有“自意识”的艺术,因而不入美学之法眼。然而,艺术的历史沿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单一线路而发展,这种进化史观已不足为信了。历史很可能是“退化史”,因此在进化史观之前,人类早已有了“退化史观”。老子和庄子就是中国古代退化史观的代表。
中国青铜器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退化的历史。古希腊雕塑被史家公认为“不可企及的范本”,这意味着在希腊之后,雕塑并无进化,甚至唯有退化。在19世纪的欧洲学院派艺术家看来,原始艺术和非洲艺术大概都是无意识的低级的艺术形态,甚至都不足以冠艺术之名,然而到了20世纪,毕加索、马蒂斯、莫迪利亚尼、亨利·摩尔等艺术大师却纷纷取法于原始艺术和非洲艺术,促成了欧洲艺术的现代转化。一时之间,原始艺术和非洲艺术似乎才是高级艺术,欧洲传统艺术反而成了低级艺术。由此可见,对民间艺术的认识往往会左右对艺术的理解,甚至决定艺术的定义。早在1894年,德国艺术学家格罗塞(Ernst Grosse)便已宣称:“艺术科学研究者如果还不明白欧洲的艺术并非世间唯一的艺术,那就不能原谅了······除非它自甘愚蒙,它已不能再不顾人种学上的种种材料了。”把这句话中“人种学上的种种材料”改为“民俗学上的种种材料”,恐怕也是成立的。
青铜器《利簋》。艺术的历史沿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单一线路而发展,这种进化史观已不足为信了。历史很可能是“退化史”。青铜器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退化的历史。
不错,金字塔的各部分确实有上下或高低之分,但金字塔是一个整体,尖顶建立在底部之上,塔尖与塔基具有连续性。强调连续性的杜威(John Dewey)有个漂亮的比喻:“山峰不是无所支撑地漂浮着的,它们甚至也不是仅仅被搁置在大地之上。就它们乃是大地的诸明显运作中的一种而言,它们就是大地。”民间艺术是艺术的基础层次,因此,忽略了民间艺术的美学研究实乃“无根的学问”。张先生呼吁建立艺术学,并且主张:“思辨型的哲学美学固然要研究,应用型的艺术美学也要研究。美学从书斋中走出,下到艺术中来,既为艺术增添了活力,也为自身补充了营养。”美学“下到艺术中来”,便成了艺术哲学,亦即广义的艺术学。黑格尔已经尝试让美学落地,“下到艺术中来”了,正因如此,今道友信将黑格尔誉为“艺术学的鼻祖”。但黑格尔将艺术局限于“美的艺术”,根本不考虑实用艺术或民间艺术,其视野未免不够开阔,因此他只能将美学变为艺术哲学,而不是变成“一般艺术学”。
张先生希望艺术学更接地气一点。在张先生所设想的艺术学学科体系中,最接近艺术哲学的是艺术原理。艺术原理可以涉及两个层次:经验性艺术原理(如托尔斯泰《艺术论》)和哲学性艺术原理(如杜威《作为经验的艺术》),哲学性的艺术原理亦即艺术哲学。可见艺术原理是“上天”或“通天”的学科。如果说艺术原理是“顶天”之学,那么,民间艺术学就是“立地”之学。艺术学的学科体系以艺术原理和民间艺术学为两端,好比是“顶天立地”,而艺术学也便站立起来了。
二、民间艺术学与艺术学的广度
金字塔越是接近底部,就越是宽广。张先生的艺术视野非常开阔,甚至涵盖了许多“准艺术”:如木石花鸟的赏玩、群众性的饮食文化,以及被称作“消闲文化”或“大众娱乐”的通俗音乐、卡拉OK等。这些“准艺术”一般不划入艺术范围,但也不能否认带有一定的艺术性。张先生所说的这些东西,大体上可以归入通俗艺术的名下,与民间艺术共同构成艺术金字塔的底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艺术理论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拓展艺术概念的边界、扩大艺术外延的过程。20世纪下半叶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开始为通俗艺术辩护,逐渐将张先生提到的这些东西纳入艺术的范畴。尤其是在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和乔治·迪基(Gorge Dickie)的艺术哲学之后,理论家放弃了以往不假思索地以“审美”界定艺术的学术进路。1964年,迪基发表了《审美态度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Aesthetic Attitude )一文,其弟子卡罗尔评论道:“迪基的《审美态度的神话》这篇论文,最好被解读为是对‘审美’观念的摧毁,这样做的目的,最终就是为了去颠覆艺术的审美诸理论——从而为他的艺术惯例论铺平道路。”此后,艺术理论得以摆脱了“审美”的桎梏,有些还向艺术社会学转变,于是对通俗艺术越发宽容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张先生的视野与西方当代艺术理论隐然相通。
这里涉及“审美”和“艺术”的关系问题。民间艺术和通俗艺术以前被贴上“不登大雅之堂”的标签,就是由于“审美性”不够突出。相反,处于金字塔尖顶的“纯艺术”,则是审美性最为突出,甚至仅为审美而存在的“唯美主义”艺术。“唯美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思潮在19世纪末才发生,但它的思想源头在 18 世纪便已埋下。1746年,夏尔·巴托(Charles Batteux)的著作《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出版,正式提出了“美的艺术”概念,这个概念涵盖诗、绘画、雕塑等七种艺术形式。此后,“美的艺术”概念进入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例如黑格尔声称:“把美学局限于美的艺术也是很自然的。”黑格尔认为美的艺术出自自由的心灵,康德则主张美的艺术出自天才的创作,康德主张:“美的艺术不能不必然地被看作天才的艺术”,“美的艺术只有作为天才的作品才是可能的”。在康德那里,与“美的艺术”相对的乃是“手工艺”,而我们知道,民间艺术的核心正是手工艺。康德对手工艺的评价并不正面:“它能够作为劳动、即一种本身并不快适(很辛苦)而只是通过它的结果(如报酬)吸引人的事情、因而强制性地加之于人。”
康德和黑格尔都把自由视为美的根源。在他们看来,手工艺意味着辛苦的劳动,而且往往是“为稻粱谋”的劳动,因而是自由的对立面。自由的阙如意味着美的缺失,康德认为手工艺的过程并没有审美经验(不快适),手工艺品中也缺乏审美价值。可是,同样是看到了手工艺的辛苦劳动,20世纪日本“民间艺术学之父”柳宗悦对民间艺术的评价却截然不同;有了柳宗悦的高度评价,民间艺术的地位才得以确立。但这已经是后话了。无论如何,康德将艺术与天才捆绑在一起,对后世的艺术理解影响巨大。艺术天才总是少数,这些少数天才是审美趣味的立法者,而且天才作为精英总是大众的对立面,这正是“唯美主义”的基本观念。艺术史家威廉·冈特(William Caunt)在描绘19世纪末欧洲的唯美主义思潮时指出:一种“把标准定在众人之上,使之与众人分离”的精神实质,导致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分离。
艺术家与众人分离开来,艺术也与日常生活分离开来。与日常生活相分离的艺术,其最佳去处就是博物馆或美术馆。与唯美主义思潮大致同时,也是博物馆或美术馆兴起的时期。因此,一方面是天才美学或精英美学,另一方面则是“博物馆美学”。20世纪的一些美学家如杜威、伽达默尔、伊瑟尔都曾经批判过这种分离式的“博物馆美学”。不过他们也都没有意识到,唯有民间艺术学才能真正突破天才美学与博物馆美学之窠臼。
唯美主义是“为艺术而艺术”,民间艺术是“为生活而艺术”。唯美主义艺术的至高使命是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民间艺术却从一开始就不是审美对象,它们是生活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民间艺术也会被当作审美对象,尤其是美学这一学科已然深入人心之后。柳宗悦便是把民间艺术视为审美对象,从中分析出诸如“不二美”“奇数美”“无事之美”“不完全之美”等颇有意思的概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总体上说,作为审美评价的对象,民间艺术是比不上纯艺术的。以康德、席勒、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已经确立了美的原则:美根源于自由。例如席勒给出定义“美是现象中的自由”,黑格尔说:“只有靠它的这种自由性,美的艺术才成为真正的艺术。”
中国美学家也纷纷效法,李泽厚说“美是自由的形式”,高尔泰说“美是自由的象征”,潘知常说“美是自由的境界”,如此,等等。如果接受了“美根源于自由”这一美学基本原则,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民间艺术的“审美性”确实不及纯艺术。民间艺术与生俱来的实用性限制了它的自由度,降低了它的审美性。民间艺术作为“低级艺术”对美学的意义不大,它不被美学家纳入体系,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民间艺术是否要从美和审美的角度去判断?
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高尔泰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美学家,被视为美学四大派之“主观派”的代表,在文集《美是自由的象征》(1986)中提出“美是自由的象征”之命题。
在柳宗悦看来,民间艺术依然是审美对象,只是他认为,西方美学体系对于解释民间艺术显得捉襟见肘,有必要从民间艺术学出发探索一种“东方美学”,这种东方美学的哲学基础是佛教哲学,所以他又称之为“佛教美学”。尽管如此,柳宗悦仍然接纳了西方美学的基本原则,主张“自由才是生出美的母亲”。同时,他也看到了东西方对“自由”的理解颇有不同,宁可用“自在”替代“自由”,主张“‘自在美’的说法更为妥当”。他说:“‘自在’永远是美的根源,是美的本质。这条法则是不变的。”“一切美,都是自在之美。美失去了自在,就不再美。”然而,“自在”是源于佛教的概念,是“心无挂碍”、自然而然之意。柳宗悦经常提到临济禅师的名言:“无事是贵人,但莫造作,只是平常。”不造作和平常心,说的都是自在而非自由。禅宗思想上通道家。造作即“有为”,而老子讲“无为”。牟宗三指出:“有为就是造作。照道家看,一有造作就不自然、不自在,就有虚伪。”
因此,一旦用“自在”替代了“自由”,“自由”的内涵便发生了变化,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自然。于是可以推论,民间艺术的基本原则并非自由,而是自然。庄子在“梓庆削木为鐻”的故事中,将这一原则表述为“以天合天”。由此看来,柳宗悦的民艺论不但没有走出美学的范围,也没有真正走出西方美学的范围。一旦我们意识到美(和美的艺术)的基本原则是自由,而民间艺术的基本原则是自然,那么我们就可以让民间艺术与美学完全脱钩。
柳宗悦《茶与美》。柳宗悦(1889-1961)创造了“民艺学”这个概念,并初步奠定了民间艺术的理论基础,被誉为“日本民艺学之父”。在《茶与美》中,柳宗悦主张“自由才是生出美的母亲”。
民间艺术可以与美学完全脱钩,那么艺术能否与美学完全脱钩呢?这是民间艺术学向艺术学提出的问题。笔者比较倾向于给出肯定的回答。笔者认为,艺术学若要真正获得独立,那就必须彻底挣脱美和审美的羁绊。20世纪确实有一些艺术哲学家主张,谈艺术未必要谈美,但我们还要更坚决地主张,谈艺术不必谈美。如果艺术作品只是审美对象,那么艺术便也只能是美学的研究对象了。
为此,有必要用艺术经验、艺术作品、艺术价值这些艺术学的概念,来替代审美经验、审美对象、审美价值这些美学的概念。当然,美学家仍然可以对艺术进行审美方面的研究,只是同时要意识到,这种研究较之艺术学是较为狭隘的。例如一幅绘画,可以做图像学的研究,或做社会学的研究,都可能与美学没什么关系;一幅画的图像学意义或社会学意义并不等于审美意义,甚至是审美意义之外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大于审美价值。总之,民间艺术让艺术从“美的艺术”或“天才的艺术”中获得突破,在事实层面延展了艺术学的广度;民间艺术学揭明艺术在美和审美外的独立地位,这在意义层面延展了艺术学的广度。
三、民间艺术学与艺术学的纵深
古代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作为学科的美学,但是有相当丰富的美学思想,体现于诗论、画论、书论之中。在古代中国,也存在着天才与大众的分离,以绘画为例,主要表现为“士人画”和“画工画”的对立。苏东坡提出“士人画”的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挞、皮裘、槽栃、刍秼,无一点骏发,看数尺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东坡题跋》下卷《又跋汉杰画山》)苏东坡《王维吴道子画》诗云:
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
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
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
······
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
摩诘得之以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
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苏东坡明确地将“士人画”与“画工画”对立起来,并将“士人画”置于“画工画”之上。意味深长的是,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作品被苏东坡归入“画工画”之列,而诗人王维则是“士人画”的首席代表。苏东坡的评价标准显然是文人审美趣味。“画工”不就是手工艺者吗?“士人画”与“画工画”相对,两者约略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高雅艺术与民间艺术。一百余年来的学者们都已经怀疑民间艺术(通俗艺术)与高雅艺术的区分。我们不能说只有肖邦的钢琴曲才是音乐,而民谣、爵士乐、黑人灵歌等不是音乐。同样的,如果我们接受了苏东坡的“士人画”观点,那么中国画就只剩下文人画了,这恐怕要将中国画的历史砍掉一半,将中国画的领土缩减三分之二。院体画难道不是中国画?敦煌壁画难道不是中国画?永乐宫壁画难道不是中国画?杨柳青年画难道不也具有中国画的某些特征吗?文人审美视野是对中国画的一种刻意窄化。
张先生说:“真正的民间艺术是与过去士大夫的所谓‘赏玩’有着显著的区别,它不是为了迎合少数人的好奇,也不是专供少数人消遣。民间美术应该严格地与小市民、士大夫的美术区别开来。”但张先生主张民间艺术不同于文人艺术,是着眼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原则,也是提醒我们不能忽视民间艺术的存在。张先生认为,中国艺术传统由宫廷艺术、文化艺术、宗教艺术、民间艺术四个分支构成。这种四分法,比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的二分法手法更细致、视野更宽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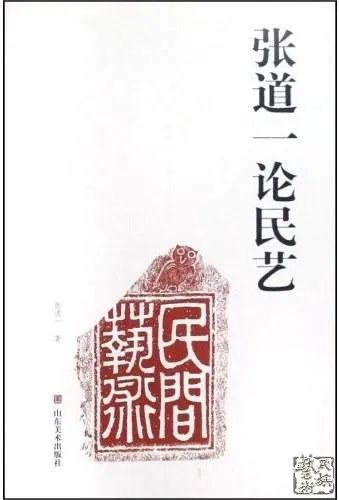
《张道一论民艺》。张道一先生认为,中国艺术传统由宫廷艺术、文化艺术、宗教艺术、民间艺术四个分支构成。
结 语
本文从张道一先生对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构想出发,引出民间艺术学与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艺术原理和民间艺术学的关系:艺术原理是一切艺术研究的基础,而民间艺术是一切艺术存在的基础;艺术原理是艺术学的顶部,民间艺术学是艺术学的底部;前者顶天,后者立地。把民间艺术学视为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最后一个子学科,使艺术学得以“站在自己的脚跟上”。
第二个层次是民间艺术与艺术的关系,这相当于20世纪之后西方学者所思考的大众艺术与精英艺术的关系。民间艺术和通俗艺术(大众艺术)形成艺术金字塔的底部,纯艺术或美的艺术处于金字塔的顶尖。20世纪之前的西方美学只关注美的艺术,今天我们重审民间艺术的意义,可以拓宽艺术研究的视野。另外,美的原则是自由,民间艺术的原则是自然,民间艺术并不是审美对象,如此我们关注民间艺术,就可能带动整个艺术研究摆脱美学的框架,使艺术学独立于美学。第三个层次是民间艺术与艺术史的关系。
民间艺术的传承性和在地性都与中国艺术史有关。民间艺术学的视野可能导致某些艺术史观点的改变,如中国绘画史的起点、流传千年的书画同源说、中国画与文人画的关系等。另外,“中国艺术学”作为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的学问,其学科归属大体上是艺术史。
来源:《民族艺术》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