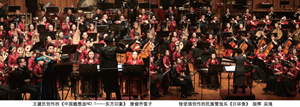“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是国家大剧院的公益性艺术教育品牌项目,自2009年秋以来,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七届。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在2009 年和2012年均参加了“春华秋实”的演出,取得了成功;2015年11月4 日,上海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团在指挥家吴强的率领下第三次登上了这一舞台,将"大音之韵"唱响于国家最高艺术殿堂。
此次演出不仅展示了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师生的精湛技艺与指挥家吴强对作品的高超诠释能力,而且全部曲目均为上海音乐学院的作曲家们在不同时期完成的优秀民乐作品。他们代表了目前仍活跃在创作上的老、中、青三代学院派作曲家的精华,作品题材广泛、技法圆熟、风格各异,呈现出中国传统乐器乐队音乐创作的广阔空间和动人光谱。
本场音乐会的第一部作品是周湘林教授的《花腰三道红》。这部作品取材于西南彝族的民族服饰及传统歌舞。在作曲家看来:“滇南彝族的歌舞保持了汉代以来的原始的踏歌遗风,曲调悠远并充满神韵,律动风趣且呈现张力。"而作品确实也兼具考古式的学术性和高度原创性的音乐想象力,尤其是体现出作曲家将视觉色彩性元素转化为音响结构的高超技艺。通过音乐的再现和再造,这些"凭灵感无法创作的优秀民歌"绝不仅是被赋予了"当代人的感受和涂抹些薄浅的印象”,而是获得了全新的诗意生命。乐队的演绎极具活力,光焰四射、热情洋溢,几乎使北方深秋的空气中弥漫了火辣的南国春意。
在这一又似序引的开门红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青年作曲家强巍昊的民族管弦乐组曲《民谣》中的《乡情》和《祭》两章。作品将民族文化的传统烙印用面、点、线意境以及它们的混合形态作为载体,植入到音画式的音响织体中。其中《乡情》一章以深切的抒情意味和优美的旋律造型让人为之动容;《祭》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作曲家极好地把握了民间祭祀中的自然主义特性与原生态精深气质,超越了民族合奏音乐固有的定式与套路,营造出一种极其新颖又接近传统美学意态的新音响。这个乐章使我们感受到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新生力量的锐气与活力。
朱晓谷教授是我国民族音乐创作领域的老前辈,也是此次演出作品的作曲家中最年长的一位。他的《江畔晨曲》是上半场的第三支曲目。作品风格圆熟、技法考究,极具描绘性与可听性。作为一部典型的民乐标题音乐作品,作曲家表达的场景是“清晨,远处传来田歌声声,如画如梦,姑娘们轻盈的脚步,拨开早春的浓雾,是去下田?还是去赶集?脚步在欢笑声中消失远去,留下田园般江南景色,带给人们无限遐想。”上海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团的演绎不仅很好地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番意境,也带来了更多丰富的联想。毕竟,这里的江南已经是昨日的记忆了,就像作品快要结束时,女高音若即若无的一声长叹那样,转瞬即逝,回味无穷。作品所呈现的那个“此情可待成追忆”的田园场景,使听者不禁深思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上半场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何训田的《达勃河随想曲》。这是一部具有经典品质、但并不经常被演奏的乐曲,是这位极有个性的作曲家在四川音乐学院求学期间完成的习作。三十年前,作品在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评奖中获得桂冠,也使当时的中国作曲界知晓了这个青年人。如果是第一次聆听这部作品,如果意识到它产生于1980年代,如果知道作曲家是何训田,大约没有人不会发出惊叹:确实出手不凡。一切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对声音及其背后的意义的理解,通过作品新奇流利的结构、惟妙惟肖的表情和原始奇幻的气韵都流露得淋漓尽致。作品虽然含有大量80年代学院派音乐的语汇,但已经完全被吸收进了这位青年作曲家的句法和谋篇布局中。曾几何时,正像白马藏族的乐舞被作曲家浓墨重彩地描画,音乐也每每被过度地言说。当我们从当今的何训田回望其创作的起点,不知收获的该是震惊和狂喜,抑或是沉思和无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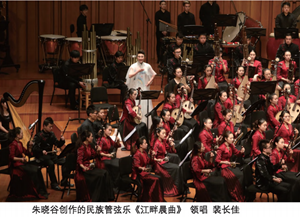
下半场开篇的徐坚强教授《日环食》,大约是本场音乐会上最具原创性和先锋性的作品,也最能带给听者全新的听觉体验和复杂的审美反思。这就像奥涅格的《太平洋231》一样,作曲家将音乐所能表现的对象第一次放置在过去的经验所无法概括的场域。这部1987年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在开拓新音响可能性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通过运用各种乐器的常规与非常规演奏法,产生出各种已知与未知的音色和音响效果,在形象地表现了瞬间即逝的非常天体奇观的同时,也表达了人对自然的各种认知与奇想。对于这样一部完全超越常规的民乐作品,乐队的演绎堪称绝佳。无疑,这也是一部值得被不断演绎和讨论的杰作。
叶国辉教授的《听江南》又将听众拉回到学院艺术的工丽细致的语境中,将现代作曲技法与传统音乐素材亲密无间地加以糅和。作品的立意在于“听”,通过最有江南特色的听觉素材,去呈现不止于聆听的地域文化要素。作曲家极为巧妙地将苏州评弹的典型音高素材进行碎片化处理,使其弥漫在人声、弹拨乐声音频响的交织中,用传统乐器的音色组合去模拟和传递了潜藏在乐音背后的语调与神情,进而渲染出这种地域文化后的经典成分与美学意趣。
将全场音乐会推向高潮的是王建民教授的竹笛协奏曲《中国随想第一号——东方印象》和作为加演曲目的《踏歌》。《东方印象》系为笛子演奏家唐俊乔量身创作。乐曲以江南一带的评弹、民歌、戏曲等民间音乐为基调,经融合、展开、创新而成。而唐俊乔教授的演奏也成为音乐会的一大亮点。这首极具技巧性的作品致力于探索竹笛的各种表现手段,并以之表现大地回春、万物萌动的景象,尤其是作曲家在作品中抒发的对于现代城市的印象,可谓民乐作品中的一个创新点。当然,让人更加兴奋不已的,是吴强指挥和乐队对于《踏歌》这一经典作品的激情演绎,这为本次“大音之韵”晋京演出画上了一个饱满的惊叹号!
这场音乐会除了许多精彩的瞬间外,理应带给我们更多思考。在这些作品所构筑的创作边界之内,其实蕴含着巨大的富矿。对于中国传统乐器所组成的大型乐队而言,从其一产生,西洋交响乐队就既是无可回避的前路,又是挥之不去的魔咒。在交响化和去交响化之间徘徊,长期以来成为学院派作曲家在这一实践领域面临的主要课题。而在欧美学院派音乐也普遍呈现去交响化的倾向之际,中国传统乐器的乐队语言,在去交响化后是否也应导向室内性,或者各种无法用西方音乐习惯定式去限制的可能,足以引发我们的兴趣与遐想。而一般“民族管弦乐”的既有成法,并不能涵盖中国音乐文化中十分丰富的地方和少数民族资源,也不能代表华夏旧乐在接受外来影响前既有的古典样态。即便是在半个多世纪的学院派实践中形成的惯用语汇,也没有像文人画和西方交响音乐那样,成为中、西文化艺术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文脉;而综观中国画和西方学院派音乐在近代的成就,往往以复古为创新的基础,才能超越窠臼,直取源头,收取老树新花之效。在促使“民族管弦乐”成为中国音乐文化的核心成分的历史进程中,学院派作曲家已经做出了许多有益尝试,一些问题通过本场音乐会呈现的作品也得到了解答,而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则必将激励后来者通过自己立足当下、兼收并蓄的创作来加以回答。
(压题图片为:演出结束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林在勇、副院长杨燕迪,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徐昌俊及作曲家朱晓谷、叶国辉、周湘林、徐坚强、强巍昊等上台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