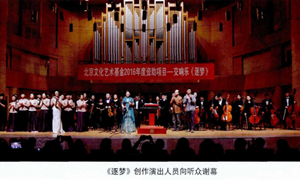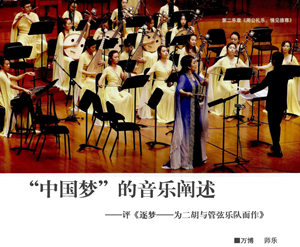
2017年6月22日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逐梦——为二胡与管弦乐队而作》音乐会,由“一通文化”平台进行了全程网络直播,观看人数逾三万。这部标题性管弦乐作品,作为一部具有宏大叙事结构与情感张力、内涵深刻且音乐意象丰富的作品,以二胡与中西管弦乐队相结合的表演形式,用管弦乐来表现中华民族由古至今追逐和实现梦想的民族精神,用音乐来诉说向往、追逐“中国梦”这一时代心声。
《逐梦》作为北京艺术基金2016年度资助项目,其主创团队由二胡演奏家宋飞、作曲家阮昆申和文案创意修海林等组成。项目负责人宋飞在创作之初谈到, “我曾期待有一部原创作品,能够通过二胡与管弦乐队的合作,在交响乐的宏大叙事结构中,发挥二胡‘擅长表达民族灵魂深处声音'的特点,去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并以这种精神激励我们自信于当下和未来。
作品通过6个乐章,择取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具典型性、代表性的题材内容,展示其人文精神及抱负情怀。乐章的标题分别是:第一乐章《夸父逐日、大禹治水》;第二乐章《周公礼乐、情见德尊》;第三乐章《孔子怀仁、大同理想》;第四乐章《中山蓝图、天下为公》;第五乐章《泽被人民、东方伟业》;第六乐章《希望田野、中国梦想》。这样一种题材内容上的创意,虽然涵盖了中华文明由古至今全历程,但其展现的要点,并非历史全程,而是基于对中华民族精神与奋斗实践典型事例的择选与宣扬。前三乐章由不同乐器编制的民族管弦乐队演奏,后三乐章由西洋管弦乐队演奏,均以二胡为主奏乐器。新颖的组合创意、深邃的信念追求、悠远的历史文脉、亲民的传播方式,使这场演出一度形成了“民乐热”。 《逐梦》曾于2017年4月11日在北京中山音乐堂首演,经北京艺术基金中期评审后,将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进行多场演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演出可以说是该作品全国巡演的开端。
一、以“乐”释“梦”——时代精神与历史人文情怀的彰显
就《逐梦》的创作和演奏而言,不仅其创作题材首先值得关注,其作品的创演从一开始就打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正如“乐者,德之华也”的经典表述那样, “中国梦”作为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已经成为时下关注度最高的艺术创作题材。但是如何用艺术作品去表现或展示“中国梦”,却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创意。管弦乐《逐梦》的创意及其表现选择在古今、中西的贯通、融合中,择取典型历史题材内容,在时代精神与历史情怀的共构中,彰显中华民族由古至今追逐梦想、勇于奋斗的经典事迹与民族精神,创作一部具宏大叙事结构与情感张力的民族交响乐作品。
在宋飞看来,二胡艺术作品中历史人文情怀的展现,可以前溯至刘天华,但历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这类作品,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初刘文金创作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阮昆申新创作的交响乐《逐梦》是一部抒发历史人文大情怀的作品,这也决定了《逐梦》的立意、创作与表演,必然具有独特的时代风格与历史情怀。
音乐以其独特的方式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人文精神与情感。就其各乐章的创意而言,其意在择取典型事例及相关审美意象,用音乐的方式对中华民族追求进步、憧憬美好理想、高扬伟大民族精神及其实践历程以展现。从创作之初,其立意就对音乐创作的构思与表现以启发,甚至在宏观布局和微观描写上,对作品乐思的展开和音响声效的建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实,音乐的创作意识,本身就包括了音声与非音声、乐音表象与语言概念不同意识活动的交互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作品在音乐艺术创作、表现的特殊性与标题性良性互动中,充分实现了标题性交响乐的美学价值,这也是乐评在传达音乐创、表现的立意、观念方面的价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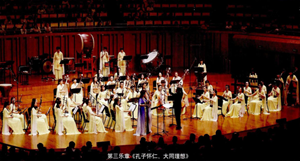
第一乐章《夸父逐日、大禹治水》,以夸父逐日永不放弃,大禹治水,造福黎民百姓为开头,奠定了坚韧奋斗,憧憬理想的民族精神基调。第二乐章《周公礼乐、情见德尊》展现的是礼乐文明的乐声之境。礼乐文化精神对其后数千年的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理想、哲学艺术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乐章《孔子怀仁、大同理想》,以给礼乐文化输入“仁”的新内容的孔子为表现对象,表现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求和、自强不息、君子修身、“天下为公”等人文精神。第四乐章《中山蓝图、天下为公》,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 “振兴中华”的理想与目标,尝试将中国带向现代化,为步入现代社会的古老国家规划蓝图。第五乐章《泽被人民、东方伟业》,歌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走向繁荣富强,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六乐章《希望田野、中国梦想》,展现的是新一代领导核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扎根于人民群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大气魄。
从美学的角度来讲,标题性交响乐《逐梦》从创意、创作到表演,均体现了音乐可以表达民族情感、时代精神与历史文化情怀。但是,作为一部交响乐作品,其艺术呈现,最终是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与诉说,因此,这部作品的创作与表演,更是评论这部音乐作品时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二、创新与诠释——“双语”的兼融与抗衡
《逐梦》在音乐的创作与表演上,给人以耳目一新、形象鲜明和气势恢宏的印象,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全曲因其题材内容的择取而由6个乐章构成,各乐章(尤其是前三个乐章)采用不同的乐队编制。因各乐章题材内容的典型性,音乐创作在以“乐”表“情”的总体思路下,从多种角度发掘其音声表现的可能性,以具有新的声境、意象的音乐语言,在传统与现代音乐语言的交织、契合与美学追求中,创造新的音声效果,诠释和塑造具典型意义的音乐风格、形象。尤其是这部作品从始至终一直萦绕在听众心中那股荡气回肠的旋律,虽各乐章的主旋律并不相同,但就象一位演奏家在音乐会后谈到的, "宋飞在与对乐队宏大的音响和结构的抗衡中,不仅以自己的声音引
领、穿越甚至包裹住了一切,更让二胡的声音超越了自己。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我再次听到了宋飞非同凡响的二胡声音。
二是这部作品以二胡为主奏乐器,二胡与乐队在这部史诗性与英雄性、抒情性与描写性兼具的大型管弦乐作品中,是在一个整体乐思的展现中与乐队做协同表达,而非伴奏与独奏的关系。上半场前三个乐章由中国音乐学院华夏民族乐团协同演奏,下半场后三个乐章由中国音乐学院青年爱乐乐团协同演奏,这样一种设置,与题材内容上前三个乐章属古代社会、后三个乐章属近现当代社会相适。这种由中西管弦乐队共同完成一部交响乐的演出,不仅在表演形式上具有新意,同时也是在“双文化”语境下,体现宋飞一贯主张的中西合璧、古今对接的“双语”创作、表演理念。
三是二胡作为民族弓弦乐器的重要代表,当面对具如此重大历史文化题材及人文内涵的作品时,其音乐的表现无论是对二胡音质的综合要求,还是音乐情感、意态与气势的表现,都提出更高的要求。此时,仅靠谱面上要求的细腻、精准或者缠绵、凄涩的情态,是担负不了这类“历史文化大情怀”的音乐表现的。只有以充沛、饱满而内力浑厚的音质,圆润、透亮而纯真谐畅的音色以及具有沁人心脾的动力性展开与旋律性歌唱,才能面对作品中历史人文大情怀的抒发和表达。

《逐梦》的各乐章,采用不同的乐队编制与配器手法,由此形成不同的乐队音响效果。就各乐章的音乐表现来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三个乐章民族管弦乐队的伴奏,采用了三种不同的乐队编制来表现特定的题材内容。第一乐章要展现的是夸父逐日的壮烈场景和大禹治水的宏大场面。但作曲家的创作却堪称举重若轻,以小见大。除二胡外,仅用了九个打击乐器、两个古筝、两个琵琶、一个埙来表现其主题。该乐章的音乐,由一静一动两个主题构成,筝、琵琶和打击乐在开始部分奏出狂野的急板,呈现的是“动”主题;与此形成对比的二胡主题,建立在五度和大七度音程上,并强调了前置的装饰音,是“静”的主题。由于将二胡定弦设为C—G,相比D—A定弦使其音色更为浑厚,内敛,在最大程度上展现了二胡音色之美。这两个主题的静动交替,在音乐上形成较大的反差与对比。正如该乐章创意文案中写到的: “从乐曲中,可以‘听’到夸父为采撷火种追逐太阳的脚步声,可以看’到大禹治水功成作乐,人们欢庆鼓舞的红火热烈场景,更可以感受到英雄造福苍生的心愿与抒怀。”第二乐章表现的是西周时周公创建的礼乐文化,其中使用了编钟、编磬这类典型的西周雅乐乐器。其主题材料取自经典雅乐曲目——《风雅十二诗谱》中的《关雎》。其单一主题的展开,主要在二胡与弦乐声部,经过5次变奏,音乐尽显其简洁、单纯。加上吹管乐,弹拨乐,再配合钟、磬的衬托,音乐风格雍容大气而富于情怀,营造出一种肃穆、典雅、祥和的雅乐气氛,塑造出周公礼乐的氛围及意象情怀。第三乐章的乐队编制,呈现的是规模宏大的民族管弦乐队。该乐章之始,由二胡引入的音乐主题经不断变化发展,绵延不断,弹拨乐则保持简单的节奏,显得安静祥和,变化的主题由弦乐引入,加厚了乐队的音色层次,音乐凝重而深远。经主题的再度变化,音乐不断发展、绵延不断,推向高潮后,再度回到志远而温暖的意境。乐队音响层次丰厚而凝重深远,展现了孔子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对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
《逐梦》的后三个乐章,采用了西洋管弦乐队与二胡相协的演出形式。各乐章的音乐主题及其变化展开可谓形象鲜明。第四乐章的整体结构为单一主题变奏。乐曲在一声悠远的钟声后直接进入主题,主题材料由纯五度、大七度构成,情绪悠远而抒情, 配器上突出了弦乐和木管的音色对比,纵向和声为二度音程叠置,形成调性、调式色彩对比。抒情的音乐主题经过八次变化及变奏不断展开。其中似感受到地火能量的聚集,并形成抗争的力量。第五乐章更像是没有再现部的奏鸣曲式结构,全曲用D为中心音。引子由圆号奏出意味深长的旋律,打击乐、铜管、弦乐的节奏如同暴风雨般强烈。坚毅的主部主题和深情的如歌慢板副部主题相互交织、变化发展。弦乐队与二胡如歌的慢版,旋律相互交织,更多运用复调写作手法。展开部的弦乐保持八分音符的节奏律动,紧张而有力。高潮部分音乐跌宕起伏、气势磅礴而充满希望,象征着济世宏愿终成伟业。作品的第六乐章一开始,引子由圆号与小号交替奏出核心材料,音乐悠远而富于憧憬。在回旋曲式结构中,音乐主题及其变体交替呈现,音乐抒情而充满希望,配器更为交响化,全曲最后铜管奏出全曲的核心材料,以辉煌而强有力的音响表达了不忘初心的意志和决心,展现了“中国梦”的美好前景。
《逐梦》音乐情感意象的塑造与主奏者宋飞在二度创作中恰当而深刻的音乐诠释有着直接关系。在这部作品中,二胡的演奏不是独奏的自我表达,而是要融入到整个交响乐的音声结构中去演奏。在音乐的叙事中,不仅要求在对音乐的解读中,对乐曲的结构、句法、调性、和声与情绪的铺陈、叙述要有很好的把握和驾驭能力。由于音乐要表现宏大的历史情感叙事,不仅对音乐的气势和力度,甚至对音头,也要象说话中的号召性语
气那种,将字头放大,形成一种恰当有力而富有弹性的音头。同时还要发挥二胡酷似人声、具有歌唱性语言诉说、表达的音响特点,让音乐具有声乐般饱满的气息和丰富的色彩。作品演出的成功,也与指挥家金野教授执棒的中国音乐学院华夏民族乐团、青年爱乐乐团中一批优秀演奏家与学生在演奏中的协同和节、倾心投入与敬业奉献分不开。《逐梦》仍有待通过整体的不断打磨,在精益求精的追求中不断升华,从而使其艺术品质日臻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