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各琵琶流派史的发展轨迹资料来看,二十世纪以来,琵琶艺术的中心,已迁移到最大的城市——上 海。就在这稍后的一段时期,“瀛洲古调派”(简称“瀛洲派”,又名“崇明派”)在北京地区也开始兴旺起来,并一直延续至现在,其间还形成了两次艺术普及和提高、相映成辉的热潮。综观国内外,艺术发展在某一地区及时间段内,总会围绕着一个代表人物的出现而展开。同样,在上述的两次热潮中,亦有两位“刘大师”出现在该乐种的制高点上:前者为我国近代民族乐器发展的奠基者,现代琵琶的开拓者,以时代手法创作出首部琵琶独奏曲并灌制唱片的刘天华先生;后者是不断改革履新,把琵琶推上国际乐坛并编创出“现代瀛洲古调”,形成独特“刘氏琵琶艺术”的刘德海先生。
天华大师 北大音传所亲身示范奠基石
天华先生是江苏江阴人,青少年时代,就参加了学校的军乐队,掌握了多种铜管乐器的演奏方法。由于生活的坎坷,较长时间在基层做教学工作,与民间艺人结谊甚深。1916年,无锡第三师范国乐队参加文艺交流,指导老师周少梅上台演奏了几曲,使天华第一次听到了《飞花点翠》这首琵琶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而向周少梅学习二胡、琵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18年暑假期间,任教于常州中学的刘天华专程赶赴南京,向东南大学教师、“瀛洲派”名家沈肇州学习琵琶技艺。沈氏一向把“以乐会友”视为乐事,对来访的乐友均以礼相待,今见天华朴实好学,更乐于为之循循诱导。他按自己汇集的、刊印不久的《瀛洲古调》谱本相授。天华艺术悟性极强,又勤奋刻苦,整天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在不到两个月内通过沈师的言传身教,学会了“小曲、文板、武套大曲”等全本《瀛洲古调》,这样的进度,令当地乐界人士深为惊佩。暑假到期,告别之际,沈师把自己所用的工尺谱本相赠,并告知:“你虽已弹完全曲,只是刚刚入门,而古调的精深处得长期研习方能悉知,切记,切记。”天华铭记在心,回常州、江阴后.不断琢磨,深化理解,音乐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次南京之行,使天华在二胡卓越成家后,琵琶技艺亦进入新的境界,从此在苏地声誉鹤起。
1922年,天华受聘赴京,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任二胡、琵琶教师。同年秋,又任北京女子高师音乐专科教师。1926 年,还兼教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和北大女子文理华院音乐系。
在长期的艺术教育中,天华用沈师所赠谱本作为基本教材,仔细标明手法、弹法的细微处及增饰的内容,特别是对列于小曲之首的《飞花点翠》。应用了增音、变奏手法,使琵琶文曲的演奏风格及秀丽的音乐语汇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遂使该曲不但成为“崇明派”的代表作,也成为我国传统乐曲中的精品名曲之一。其改编手法,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节奏安排上紧疏得当,动静有致,更能衬托其曲意:二,连续运用推挽音,勾勒出玉树临风的摇曳景象;三,以“套着走”来处置长音,致使在原先旋律稀疏处加花嵌档,填补空隙。(天华固然对该曲化了相当精力加工,但多篇文章中提到他还把此曲加长,这是不确切的,笔者另有文详述)天华学以致用,这时期创作的琵琶曲《虚籁》、《改进操》,多次使用弹擞、勾搭等手法,乐人评论“显然是受到了‘崇明派’的影响”。
1928年,德国人雷兴来到京地天华处,商议高亭公司为其录音灌片事宜。不久,公司派技工带了装置从沪来京,灌制了两张唱片,其一面是二胡曲《病中吟》和《空山乌语》,另一面是琵琶曲《飞花点翠》和《歌舞引》。雷兴深为天华所奏乐曲之感,动容地说:“这一过程中,我始终在场,清越之音使人深感有超越的情思”。能使这位身经百“乐”的制片商叹为观止,确实说明了天华技艺的不同凡响及感人至深。
在北大定期举行的音乐会上,天华选用的琵琶曲目大都来自《瀛洲古调》,他遵循“瀛洲派”有关“指力坚强而清纯,音响明快而凝重,虽绮丽而不失庄重,悲壮而不落滞涩”的艺训,用不同的方式对不同的乐曲表达不同的情意详细讲解,从而达到因“曲”施教的目的。当弹奏《十面埋伏》时,天华把预先写好的各段小标题放在台侧,由学生吴伯超随着弹奏的顺序翻动各段说明,在乐声中加深现场观众的理解。天华以“瀛洲派”特有的扫、拂、扭绞三弦、四弦等技法,把千军万马,呼号声震天的景象表达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其兄半农先生也叹曰:天华的《十面埋伏》,沈雄奇伟,变化万千,非天华魄力不能举。
1927年春,天华先生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在经济条件极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出刊了十期《音乐杂志》,对古曲也进行理论研讨,从而形成了对传统乐曲及创作乐曲的相互交流,开创“屁股坐在国乐改进社,双手伸向中外古今”相辅相成的新局面。
天华先生对西洋音乐的态度是辩证的,他表示,“一国的文化断然不是抄袭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已见而能算数的。我们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神,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东西交融及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
1926年冬,北京女子高师音乐学系学生的年终汇报音乐会假真光电影院举行,其中包括十六个女学生的集体亮相,当她们上台时,仿佛十六只花蝴蝶飞上舞台花丛中。集体弹奏委婉隽永的“瀛洲古调”时,令人耳目一新,奏后多次谢幕,欲罢不能。
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抗战时期声名卓著的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也是天华先生的学生,韩后来到美国留学,音乐系特举办“韩君权华欢送会”,别离时天华语重心长说道:“我也学过西洋音乐,那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整理我们的民族音乐,你去异国学西乐时,不要忘了国乐,望你早日学成归国,一起整理出版我国民族的音乐”。韩不忘师训,在美国不同场合弹奏琵琶时,总是选用《瀛洲古调》中的曲目,《飞花点翠》更是每次必奏曲,深得异国人士及华人的垂爱(传记影片《辽沈战役》中,就有韩权华手拿琵琶出现在卫立煌身边的特写镜头)。
天华先生在学生中有崇高的威望,学生们毕业后,分赴各地,以后在琵琶艺术传承中做出一定贡献的有曹安和、王君仅、吴伯超、肖伯清等。
正当天华先生年富力强,全力投身于发展民族音乐之际,1932年6月,到天桥收集锣鼓经时,染上猩红热,不幸病故。他的辞世,真乃我国二胡、琵琶艺术的一大损失,也是“瀛洲派”传承光大的一大损失。他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掌握民族音乐创作技法规律,而又善于吸收西洋音乐进步因素的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
天华先生留下的古调教材谱本上,详细记录了其教学心得体会,女弟子曹安和继承遗志,与表兄杨荫浏一起,于1941年合编刊印了古调的《文板十二曲》,记谱方式上有了两点突破。一是用工尺谱、五线谱两种谱式;二是用大、小两种字体:大字表示原谱,小字为实际演奏时加入的色彩花音。至今还通用的琵琶技法符号即是由此曹安和加工整理的谱本行变而来。“瀛洲古调”在乐界的影响深远,以此可见一斑。
被称为“刘天华先生最刻苦、勤奋的学生”曹安和义不容辞的接过教棒,为新一代琵琶手的成长殚思极虑。十年寒窗之下,调教出了一批高徒,其中就有佼佼者,“最值得骄傲的当代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
德海大师 古调发源地躬临调研谱新曲
德海先生生于上海,从小受父亲影响学习笛子、二胡及琵琶等民族乐器,又曾参与当地沪、越及评弹等业余团体的活动。由于对各门类艺术触类旁通,人称为“小灵灵”,通过这些艺术实践积累了大量以后在大学课堂里无法获取的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的启蒙知识。功夫不负有心人,1957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林石城、曹安和等名家,学得《平沙落雁》等快板八曲,从而叩开了“瀛洲古调”的大门。同时,还有意识的选修了鼓板、古琴和低音提琴等冷门乐器。以后有业内人士这样评说:如果没有当年业余剧团中的小灵灵,没有客串过鼓板和低音提琴的小乐手,就不可能孕育出今天蜚声海内外的刘大师。
学艺过程中跨出改革的步伐是要有非凡教力的,德海抛却门户之见,对各琵琶流派的曲目和特点均下了一番苦功,逐步成长为一名德艺双馨的国家高等音乐学府的专业教师。
虽然德海先生不以某一派嫡传弟子自居,但也坦陈对于“瀛洲派”小曲的情有独钟,对每首小曲表达的诗情曲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有“小壶中见乾坤”的收货。他逐渐领悟到古调与《华氏谱》的一脉相承,其审美核心概括为两个字——童趣,这一灵犀的点通,犹如注入了新的艺术活力和创作灵感。他把小曲编入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之中,有些学生在初学时,往往认为这些小曲“呒啥花头势”,以为只要按谱弹奏即可。经过刘师的示范及几堂课下来,才渐渐体会出小曲的特殊风味。学生葛咏亦深者所感说:“我1991年大一时,就随先生习古调小曲,直到最近在音乐会上与先生共奏,仍对“曲短而趣长,音疏而韵浓’有新的感悟。”难怪有老艺人把小曲比作“崇明老白酒”,越品越醇厚,越意味深长。
对古调中《十面埋伏》及《飞花点翠》这一武一文两首代表曲目,德海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益求精的再加工,呈现不断深入,层层递进的特点。于前者,吸取各流派的特长优势,精编成《刘德海琵琶谱》,在各种场合演奏;于后者,应用了变奏加花等手法,让“推、拉、吟、揉”各显其能,尤其在泛音应用上,更显深远,回味无穷。
德海先生对“瀛洲古调”在海内外传扬所作的努力是广为人们称颂的。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武汉举办的《全国民族乐器独奏音乐会》的开幕式上,举办方特邀刘师以大师身份临场献艺,其当即推出《蜻蜓点水》等一组小曲,引发了海内外乐界人士对这些“养在深闺人未识”古曲的极大兴趣,也为古调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吹响了进军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德海老师将八首古调小曲按四季变换汇编成一套组曲:春一一《鱼儿戏水》等;夏一一《蜻蜓点水》;秋一一《顽童》;冬一一《狮子滚绣球》等。并请名家画了八幅水墨画,借鉴当年天华大师的教习法,边奏边释边欣赏,收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为此,,德海老师戏称自已为“童心未泯,玩琵琶于掌心,玩出花样,玩出色彩,玩出家门,玩出国门”。
通过德海大师在演奏、教育、创编及理论研究诸方面的闪光点汇聚,形成了系统的“刘氏琵琶艺术”。其中“瀛洲古调”无疑也占有一定的比重,人们也津津乐道于汇合在他身上的光环及诸多第一:
一一多次为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演奏,宋氏在 1918年与中山先生在沪寓所听过沈肇州弹奏的“瀛洲古调”,故而特感兴趣,给予很高的评价。
一一屡次为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献艺,使之深叹中国民族音乐的博大精深及迷入魅力。
一一1960年,首奏独奏曲《狼牙山五壮士》,首创从大提琴移植而来的大指按弦法,突破了原先难以演奏音程跨度大且快速乐段的局限,提高了琵琶的表现力。
一一1973年,与吴祖强等合作创作了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首开了琵琶独奏曲由西洋管弦队协奏之先河。
一一三次 与指挥家小泽征尔及美国波 士顿交响乐团合作,又与西柏林交响乐团交流配合,被称为与西方交响乐团交谊的中国民族音乐第一人。
让我们跨过这些耀目的光环,把广角镜的镜头转向“瀛洲派”发源地一一崇明岛上来。
2009年冬,崇明企业家杨刚先生有意创办“杨刚民间音乐馆”(下简称“乐馆”),邀刘师前来指教。德海先生也正有往“瀛洲派”源地调研之意愿,双方所见略同,遂促成了德海大师四次的“崇明之行”。
首行一一寻根溯源 挥毫为乐馆提名
2010年4月,首次应“乐馆”邀请来崇,参加“瀛洲派”琵琶研讨会及“乐馆”开馆预展,采访了流派传人赵洪相及当地流派的研究者,既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古调小曲,又耳闻了该流派在源地上的传承历史轨迹,全面了解了流派的源、流、曲目及艺训等发展走向。德海欣然为“乐馆”留下墨宝题名,作为永久性纪念。研讨会上弹奏了经加工处理的古调名曲。
二行一一割爱献宝 赞基地后继有人
翌年4月,德海大师把自己心爱的、伴随其三十多年走遍世界各地的“蛟龙”琵琶及部分手稿赠送给“乐馆”,“蛟龙”则成为镇馆之宝之一。又与闵惠芬、顾冠仁一起参与由当地文化部门举办的“瀛洲畅想一大 师与民间乐队对话音乐会”,并与小乐手亲切交谈,盛赞琵琶“从娃娃抓起”的必要性。并准备明年带一组回归江南、反映儿童情趣及心理状态的创作曲目到传承基地上来演奏,让小琵琶手们开阔艺术视野。
三行一一-群贤毕至 新创立丝竹乐种
2013年4月,与音乐理论家乔建中,作曲家顾冠仁,“乐馆”馆长杨刚共同发起为创立新丝竹乐种一一“瀛洲丝竹”谱新曲的号召。 京、沪、宁、杭、苏、浙各地乐界代表人士纷至沓来,参加座谈会。五十多个代表畅所欲言,坦陈已见。但对创作新丝竹作品的观点是统一的。
《人民音乐》及《解放日报》等众多媒体作了专题报道,目前已收到新作品二十多首,其中《东滩晨曲》、《江南行》、《水仙》、《妈妈的爱》及改编的古调两首,作为2013年海内外江南丝竹比赛中的推荐曲目,受到了各方人士的关注和称道。
四行——童谣引题 象征着叶落归根
德海大师认为自己是“瀛洲派”传人,所以来到源地崇明,也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2013年11月,把原计划在北京举办的《刘德海从艺六十周年音乐会》转移到“瀛洲派”源地上来。刘师与八名女弟子轻装简从来崇献艺。上演的曲目既有丝竹乐,又有器乐化的民歌;既有经典《二泉映月》,又有新作《妈妈的爱》;对古调既选择了《狮子滚绣球》等小曲,又推出了武曲《十面埋伏》,当刘师与弟子们在奏前吟诵童谣“我给外婆弹古调,外婆给我吃块崇明糕”时,台上台下彼此呼应.这种别出心裁的“引题”方式,使观众们倍感亲切,仿佛回到了在外婆跟前撒娇的孩提时代。
音乐会及研讨会花絮
刘师与六弟子以七把琵琶的非凡声势奏响了新版《十面埋伏》,那横向的旋律和纵向的织体结构严密,气势磅礴,声震屋宇,引发众多乐迷起身叫好,把音乐会推向高潮。
最后一个节目是由大师亲自指挥,瀛洲丝竹乐团与刘氏弟子合奏的《三六》,接近尾声处,响起了大师寄语抒发的“画外音”:
瀛洲仙岛一一崇 明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
任然保留着农耕水乡地貌风情的一片绿洲
她,为我故乡之行的第一步落脚地
倍感亲和安详
这余音袅袅得告别之声绕于音乐会堂的糅间,给人以无穷的遐思.....
次日的《刘德海琵琶艺术研讨会》上,来自各地区的专家学者宣读了十多篇论文,与会者一致肯定了“刘氏琵琶艺术”的历史功绩及其本人在当代琵琶史上领军人物的地位,呼吁乐界人士通力合作,为迎接新一个琵琶艺术高峰时期的到来而同庆共贺。
琵琶,自从传入中原发展成一种独奏乐器之后,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乐手绽放着各异的色彩,凝结成五彩缤纷的结晶。作为一代琵琶大师的刘天华、刘德海先生的艺术生涯应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以上只是摘取某个侧面描述之。如果说,前辈天华大师于上世纪二十年代 为“瀛洲派”在京地生根、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培养出一批名家的话;那么,当今的德海大师采用古曲素材,以现代的音响和理解方式拉近欣赏者与传统古曲的距离,从而创作出“乡土风情篇”十余首被称为“当代瀛洲古调”的琵琶小品来。传统音乐的传承,不仅致力于音乐本体,而且还要注重于该乐种所蕴蓄的文化内涵的发掘、阐释和传授。达到传者能“传神”,承者能“承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传统音乐的精神实质,二位刘大师就是这样作的,为我们其他流派传承和发展树立了典型的范例。 为此,甚有必要为两位刘大师与 古调所结的情缘和贡献,在我国琵琶史上留下这“稀为贵”的一页。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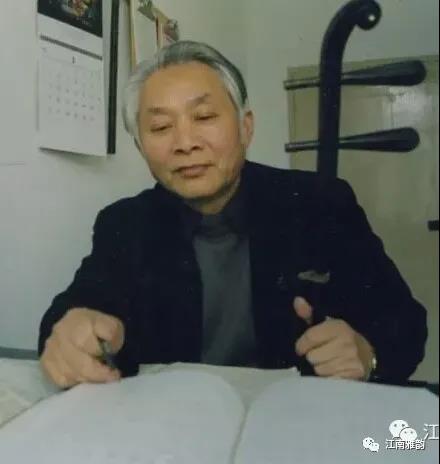
王霖(1942.8.2——2017.1.18),上海市崇明县人,副研究员。早年从事民族器乐、江南丝竹以及崇明渔歌、山歌剧的改编和创作,曾担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上海卷》的编委。出版了民乐合奏曲《打谷场上歌声扬》的总谱单行本,创作的笛子二重奏《秧机突突添锦绣》获上海市业余音乐创作一等奖,改编的江南丝竹《苏扬桥》参加了1980年上海之春音乐节的演出。八十年代后转为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包括对唐乐器“忽雷”、《夕阳箫鼓》作者的探究等,特别是对琵琶四大流派之一的瀛洲古调及其传承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在中国音乐界顶尖核心刊物上发表了《瀛洲古调派探源》《瀛洲古调派琵琶流支及风格述论》《瀛洲古调派两传人的姓名质疑》《琵琶瀛洲古调派发源地所见曲目》、《唐宫秘器大小忽雷觅踪》《〈春江花月夜〉曲源及作者探究》《疏忽一时抱憾归,徘徊廿载今揭晓——〈夕阳箫鼓〉》曲作者及有关疑题的再探究》等相关论文20多篇。出版了 专著《瀛洲游思集》上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