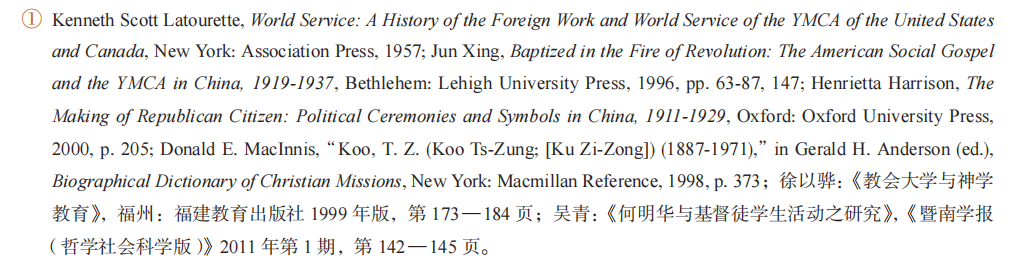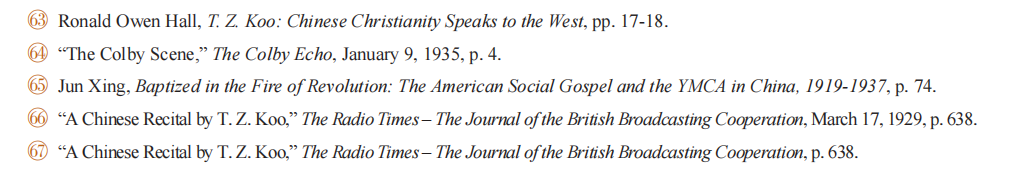摘要:顾子仁作为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创始人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不仅在1920至1950年代的国内学生界叱咤风云,在世界学生基督教界也享有极高的声誉。自1920年代起,他在全球近五十个国家巡回演讲达三十余年。出身于教会学校,但“酷嗜”中国民间音乐的顾子仁“每于公开演讲之先,出其袖中所藏的短箫,当众吹奏一曲”。顾氏在域外吹奏的曲目均来自其1928年编辑出版的中英文歌(乐)曲集《民间音乐》。虽然顾子仁是民国时期最早将中国民间音乐传播域外者,也是最得力且最有影响者,但国内外学界无论对其人或其在海外传播中国传统及民间音乐之事工都没有专门的研究。文章拟通过稽查中西文档案文献,北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亚、新加坡及印度当时之新闻报道,搜罗海内外有关的研究来对顾子仁在海外介绍中国民间音乐之史实及其影响做一陈述。
关键词:顾子仁;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民间音乐;海外中国音乐研究;域外传介
引言
顾子仁(TsZungKoo,常简写为“T.Z.Koo”,1887—1971)这个名字,除了专门研究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少数中国近代史学者和关注中国基督教圣乐本土化的专家偶有提及外,[1]知道的人可能不会很多,尤其是在近现代音乐史学界,顾氏可以说是个完全被遗忘的人物。虽然自1920年起,他即以中国青年协会代表和世界学生基督教同盟干事的身份开始在世界各地“奔走旅行,巡回演讲之中,席不暇暖,大有墨翟‘腓无胈,胫无毛’之概。……旅行欧美各国先后达二十年”“环绕了地球至少四次,巡访过千万所学校”,足迹遍及近五十个国家,尤其是在北美洲他演说家的声誉更是如日中天。“他早于一九二七年从纽约州的柯格德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头衔。后来又有两间大学(DenverUniversityandLewisClarkUniversity)赠以博士学位。‘Dr.T.Z.Koo’的大名,在美国真可谓‘家喻户晓’”。[2]更有意思的是,“酷嗜音乐”的顾子仁“每于公开演讲之先,出其袖中所藏(顾氏经常着中国长袍,甚至在欧美旅行亦然)的短箫,当众吹奏一曲,抑扬顿挫,潮落波兴,使会众先以心动神怡”[3]。至迟在1928年,即赵元任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被誉为“‘五四’以来第一部融会中西音乐艺术的歌集”[4]的《新诗歌集》、李伯英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其所编《民间十种曲》的那年,出身“通常不大注重国文”的教会学校、英文比中文好[5]的顾子仁就“将中国民间流行的歌曲,选采其典型者,一一调为西方式的五线乐谱”[6],编辑出版了日后在海内外广为流传的中英文本《民间音乐》[7]。虽然顾子仁是民国时期最早将中国民间音乐传播域外者,也是最得力且最有影响者,但国内外学界无论对其人或其在海外传播中国传统及民间音乐之事工都没有专门的研究。除了与顾子仁“有五十多年的友谊”,且“曾经多年共事”的老友——哲学家、基督教思想家谢扶雅(1892—1991)在顾氏逝世后对顾氏其人及其《民间音乐》有所简介外,国内外学界不仅迄今仍没有任何专门的研究,就连近代史辞典(如《民国人物大辞典》)和音乐辞书(如《中国音乐词典》)也未列有关他的词条。
学界对顾子仁的忽视应与相关中文史料的缺乏有关。事实上,顾子仁因为“大部分生涯都在奔走演讲中度过”,晚年又“在美国若干高等学府授远东问题及中国文化”,[8]其在域外的声誉比在国内更为昭著,因而与其相关的西文史料相对来说要更多、更全面些。本文拟通过稽查中西文档案文献,北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亚、新加坡及印度新闻报纸,搜罗海内外有关的研究来对顾子仁在海外介绍中国民间音乐之史实及其影响做一陈述。
一、顾子仁其人及早年经历
笔者知道顾子仁,应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最初是因为在美国俄勒刚大学(UniversityofOregon)图书馆网站上偶遇了数字化了的顾氏编辑的中英文双语版《民间音乐——中国各地当今流传的歌曲选集》第4版[9];之后又邂逅了谢扶雅1973年编著的小册子《顾子仁与学运》[10],该书辟有“顾著《民间音乐》”一章。但是真正对顾氏产生探幽穷赜的兴趣,还是笔者在惠灵顿国家图书馆看到以下这几张照片(见图1、图2、图3)和有关顾氏1927年至1941年间多次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巡回讲演的报道之后。[11]

顾子仁1887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基督教世家,[15]父亲顾春林系圣公会按立牧师,曾执掌上海邻县嘉定西门外圣公会善牧堂,[16]弟弟是曾在北平国立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任职的著名图书收藏家顾子刚(1899—1984)。[17]顾氏中学毕业后即进入美国圣公会所办的圣约翰大学,主修神学课程,[18]“亦习音乐”[19],并曾参加学校演出的莎士比亚剧作。[20]“他虽然从教会学校习得演奏钢琴,但他爱中国的乐器,好以一枝(按:应为‘支’)短笛相随”[21]。1906年,19岁的顾子仁大学毕业后,秉着教育救国的理念远赴四川成都的一所中学执教。一年后,他认识到做实业,特别是修建铁路远比教书育人重要,随即转就川汉及津浦铁路总局,担任洋文秘书一职,一干就是十年。[22]1917年,应他圣约翰高班同学、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1882—1936)的邀请,顾子仁来青年会上海总部襄理总务,次年即升为中国青年协会副总干事兼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学生部执行干事。在沪期间,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与蒋梦麟、余日章、朱友渔及李耀邦一起为当时寓沪撰写建国大纲的孙中山“斟酌其英译文句”[23]。自1920年起,他即以中国青年协会副总干事的身份,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TheWorldStudentChristianFederation)总委员会的各方领袖相互动,同时也代表余日章赴欧洲、美国及印度参加国际学生会议,[24]自此登上了世界大舞台。
1921年6月,通过顾子仁的努力,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执行委员会在荷兰举办的年会上议决,[25]1922年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26]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此专门成立了筹备委员会,顾子仁因其出色的口才和组织能力被推举为筹备会总干事。他与北京及各地青年会中西人士协力,选定清华学校为举行该次大会的地点。1922年4月4日—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清华园召开,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丹麦、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德国、日本,以及东南亚等32个国际和近东地区的学生运动领袖,连同600名中国学生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27]此前,他于1920年和1921年代表中国基督教学生赴英国和日内瓦开会。由于工作出色,顾子仁得到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长,后来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约翰·穆德博士(DrJohnR.Mott,1865—1955)的赏识,[28]特别是顾氏的英文演讲能力给穆德的印象最深,用穆德自己的话说:“他是我听过的最为清晰、最富有说服力、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东方演讲者之一。”[29]
二、从中国青年会干事到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副会长
1924年,顾子仁再次被基督教中国青年会派到英国考察基督徒学生运动,回国后,在学生运动方向问题上,顾氏与时任中华基督教全国协会会长的余日章产生了一些分歧。为了施展自己的主张,也为了不与提携他的余氏产生冲突,顾氏“于1920年代的下半段起,特由青年全国协会学生部告退”,而转任总部在日内瓦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一职,[30]从而开始了他常年在海外巡回演讲的职业演说家的生涯。
除了组织和参加大型国际会议及到海外考察外,顾子仁此间主要参与了基督教青年会1912年在上海创设的青年协会书局的编辑和出版活动。也就是在青年协会书局工作期间,顾子仁意识到,要想让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就必须从中国的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来解释基督教义,因而对编辑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赞美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在《教务杂志》上发表相关主张外,[31]他还开始利用在全国各地考察和演讲的机会广泛收集中国民间歌调,[32]并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第十一届大会会议赞美诗集《赞美诗歌》(1922)中发表了他创作和编配的赞美诗。[33]顾子仁也是民国期间最早为西洋经典赞美诗配置中国旋律的中国人。早在1920年代,他就将英国诗人、思想家、《失乐园》的作者约翰·弥尔顿(JohnMilton,1608—1674)早期创作的《欢然颂主歌》(LetuswithagladsomemindpraisetheLord)配上中国五声音阶旋律,发表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圣诗集《向主唱新歌》(CantateDomino)上(见谱1)。

1927年,顾子仁增订了谢洪赍、谢扶雅、胡贻谷等编辑的《青年诗歌:附赓歌集》[35]。1928年,他又将谢洪赍1908年首版的赞美诗集《青年诗歌》增订为《有谱青年诗歌》[36],由青年协会书局出版发行。同年,顾氏还和时为沪江大学校长的刘湛恩(1896—1938)一同编辑出版了收有46首圣歌、附钢琴伴奏谱的《新公民诗歌》[37]。1928年,顾子仁编辑的《民间音乐》在上海出版(见图4)。《民间音乐》虽然不是基督教圣歌集,但也显示了顾氏基督教本土化的企图。在该集的“序言”中,他明确指出编撰此歌集的初衷及宗教歌曲在其书中所占的比例:

一民族之文化常与其音乐有密切关系。是故伟大民族。必有伟大音乐为其背景。吾人而欲认识一民族之真精神。玩赏其音乐。吟诵其诗歌。实为最好法门。吾国古乐用意高深。能了解其旨者止极少数人。殊难普及于一般民众。顾吾民族的音乐为吾民族文化之所寄托。发扬而光大之。实为急不容缓之要图。编者于国乐素鲜研究。惟于旅行南北各地时。见各地莫不有本地风光之歌曲。深觉可爱。辄为从事采集。就其音调而制为五线曲谱。系以适应现代思想之词句。以便普遍适用。……吾国基督教会之需求本色化之诗歌。已非一日。而应者迄今寥寥。致使教会所歌咏者。仍不外他国人心灵中之产物。与吾国人之灵性需要。颇多不想(按:应为“相”)吻合之处。深可叹息。吾尝谓吾国教会不欲谋求真正的自立而已。苟其欲之。必自产生本色的诗歌始。是编所列各什。含宗教气味者十不一二。然于此略示端倪。使后起者知所用力,而完成中国教会本色诗歌的大业。则尤所馨香祷祝者也。[38]
《民间音乐》首版所收的21首曲目为:《梅花三弄》(器乐组曲)、《孔庙大成乐章》(六章)、《中秋闺怨》、《天下为公》(万年欢调)、《板桥道情》、《凤阳花鼓》、《思美人》、《紫竹调》(箫)、《哈喇潞呀》(佛教曲调)、《四季相思》、《叹十声》、《壮哉五四》(十杯酒调)、《大国民》、《美哉中华》、《小白菜》、《苏武牧羊》、《爱国五更》(叹五更调)以及《乞丐自叹》《孟姜女》《望妆台》《我中华》。很显然,顾子仁是要把中国各地具有地方色彩的汉族民间音乐介绍给西方音乐爱好者。在遴选的种类上,既有庄重典雅的孔庙乐章和佛教唱诵曲调,也包括节奏鲜明的民间舞曲;既有从民歌发展而成的曲艺《板桥道情》和传统的闺帏相思曲《中秋闺怨》,也有城市流行的小曲;既有古代经典器乐曲,也有近代“全国各地传唱最广的学校歌曲”[39]《苏武牧羊》和爱国歌曲《满江红》。在所选歌曲的流传地域上,既有安徽北部的《凤阳花鼓》,也有遍传华夏的《叹五更》《孟姜女》以及江南独有的《紫竹调》、华北的《小白菜》。
在回忆起顾子仁“为何编行《民间音乐》”时,与顾氏“道同志和,义逾弟昆”的谢扶雅认为顾氏是为了呼应孙中山“唤起民众”的教诲,而利用其音乐之长去首先唤起中国青年的良知的:
子仁深知男女学生青年,热情像一团火,最好是让他(她)们明白中国民间的疾苦,与老百姓的颠连无告,而激发其同情心。所以孙中山所迫切要求的“唤起民众”的大业,惟有全国青年足以膺此巨坚,而亦再适宜不过的事。……擅长音乐的子仁,便运用了此道去打动青年学子同胞物与的心弦。他不用自作新曲,他只消利用中国民间固有的歌谣——那些饱受剥削、敲吮、压迫、无可奈何,只好怨命诉苦于歌谣,将它们一一谱之于新式的线谱(这比之使用西洋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发扬民族菁华,有何逊色?)在集会中宣唱出来,精神上便与苦命的老百姓同在,而你便不由不披发缨冠,奋往援助。[40]
此话不谬。但除了“唤起民众”外,《民间音乐》更有意义的是其出版后在海内外产生的影响。
《民间音乐》1928年7月在上海出版首版后深受欢迎,不到三年就有至少两种版本,到1931年10月已印行至少五次。用谢扶雅的话说:“这书于五年之间重印四版(通常每版一千本),就当年来说,可谓洛阳纸贵,销行甚速而普遍,可能基督徒学生间已是人手一编了。”[41]的确,《民间音乐》不仅同年11月即再版,同时也得到中外同行的认可和推荐,如美国浸礼会来华传教士、曾任沪江大学教育学和音乐教授、时任上海美国学校校长的埃兰姆·安德生(ElamJ.Anderson,1890—1944)当年10月就在美国教会在华的机关英文出版物《教务杂志》(TheChineseRecorder)上撰文推荐,盛赞顾子仁“不仅为自己的人民,而且为所有真心实意希望了解具有代表性中国民间曲调的西方人提供了不少帮助”。安德生还特别提到顾子仁为中国民间乐曲配和声的尝试:“任何试图为中国旋律配和声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热烈地祝贺顾先生为这些歌曲编配的四部和声的成功,这样一来这些曲目就可用钢琴或风琴演奏了。虽然他谦虚的声称,他没有受过音乐训练就这样做了,但这只会使他的成就更值得瞩目,因为他配置的和声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出色,保留了大多数中国旋律的小调特征。”“所有音乐爱好者都会对这一歌集感兴趣并因此受到激励,因为对该歌集的研究将使西方人和中国人通过西方记谱法这一媒介了解到中国和西方音乐的一些异同。”[42]安德生对《民间音乐》的好评并非只是客套话,而是一个有多年在华音乐教育经历过来人的由衷之言。早在1923年,时任沪江大学教育学和音乐教授的安德生就已经编选出版了“辑有中外学校校歌世界各国国歌以及西洋家弦户诵之曲”凡104首的英文《中外学校唱歌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在全国出版发行。[43]
顾子仁的《民间音乐》出版后的影响也非常大,他所选用的一些中国传统曲调也被他之后的一些圣歌编撰者引用。如1931年,燕京大学赵紫宸(1888—1979)和范天祥(BlissMitchellWiant,1895—1975)合作出版的《民众圣歌集》中的曲调,有些就来自顾氏的《民间音乐》。范天祥在其书中的序言里就坦言说:“本集所收的调,皆系中国旧调,未经丝毫的修改。这些调子或出于顾子仁博士的《民间音乐》,或出于王女士的《小白菜》,或是胡杜两牧师所采集的民歌。”[44]据说钱仁康先生1930年进入无锡师范学校后,“为了检验和声在音乐创作中的运营效果”,还曾“为顾子仁编的《中国民歌》逐一配上了钢琴伴奏”。[45]据谢扶雅回忆,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青年协会学生部干事刘良模(1909—1988)“组织了一个歌唱团,走遍后方和前线,发扬蹈厉,鼓舞全国军民持久奋斗的精神,效献于中华民族的保全与复兴者甚大。这,无疑地是受了顾氏《民间音乐》一书的提示和影响”[46]。
1931年,顾子仁除了出版《民间音乐》第五版外,还编辑有《海外心声》一集,由开明书店出版。此歌集收有《伤风歌》《西风徐徐吹》《游兴》《神在法相》《吾爱吾将守护弥殷》《七哀诗》《甜蜜的好梦》《杂诗》《主赐晚安》《铃铃歌》《夏夜美景》《念奴娇》12首中外歌曲。[47]1930年代初,顾子仁还在萧乾(1910—1999)和美国青年安澜(WilliamAllen)在北京编译出版的英文周刊《中国简报》(ChinainBrief)上发表过他为《我带小妹去逛花灯》之类民间爱情歌曲“配上了爱国的新词”的《大众之歌》。[48]
顾子仁1928年被提升为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副会长兼巡行干事,此后他为同盟会到全球各地巡访讲演。193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副会长任期满后,[49]顾氏继续担任该同盟会的“特派员”(specialworker),[50]直至1947年年满六十岁时才荣退。在担任此职的“逾二十年”期间,顾氏“环绕了地球至少四次,巡访过千万所学校”(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密歇根、牛津等欧美名校),“对青年群作了无可数计的讲演”。在这“二十余年周游寰宇的期间,前半段,子仁时常有机会巡行中国,自平津至关外,自大江南北至华南;后半段则因中日战争而主要在欧洲之英、法、德、北美洲之美及加拿大,都是他足迹常经之地,而南太平洋地域澳洲、纽西兰、印尼,也是他屡次巡回讲演的场区”[51]。其声名之大“所到之处无不大受一般人士所钦佩,为国人在国际地位上不可多得之人物,国内学子稍留心国际和平问题者,无不知其大名”。更重要的是,顾子仁“非但人格学问口才蜚声中外,即对于中国国乐,亦精究其深,……精吹洞箫”。[52]这也是“他之所以蜚声寰宇,成为家喻户晓的国际闻人”[53]的原因之一。的确,顾子仁的讲演之所以深受欢迎,是因其有一独特之处,那就是他的着装(“他总是披着中国的蓝色大袍”,顾氏自1920年后就不再穿西装)和吹洞箫。顾子仁几乎在其所有的演讲之前或演讲完后都会“自袖中出其心爱的箫,吹奏一曲抑扬顿挫,悱恻动人”[54]的东方曲调,“使会众在未听他讲演之前已震撼了心弦而倾心拜服”[55]。音乐教育家李抱忱(1907—1979)在中学读书时代参加学生夏令会时就曾听过“顾博士奏箫好几次,真是如泣如诉”[56]。
现今可查到的有关顾子仁海外讲演的英文报道大多都会提到他的洞箫演奏。如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报纸《广告人及注册》(AdvertiserandRegister)1931年3月19日的报道就是这样提到顾氏在阿尔弗雷德王子学院所做的演讲的:
通过演示中国音乐,顾子仁博士对阿德莱德高中男生说:“中国音乐绝非像有些人形容得那样‘就好像将九只猫放在一布袋内,由一人使劲踩而发出的噪音。’”顾博士拿出一枝由竹子制成的、名为“洞箫”的长笛(他说,这种乐器在中国用不了多少钱就可买到)并演奏了几首中国民歌。第一首是名为《叹五更》的伤感的小曲,如乡村青年人唱给他爱人的恋歌。“现在”,顾博士说,“我给你们演奏一首真正的情歌。此歌名为《思美人》,其特点是结尾处的延长音。”他指出:“西方情歌和东方情歌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情歌是关于婚前之情爱,而后者的情歌往往更注重婚后之恋情。”之后,他吹奏了一首讲述小女孩失去母亲的乐曲《小白菜》。最后,顾博士模仿敲鼓声演唱了一首名为《凤阳花鼓》的幽默的中国歌曲。[57]
1931年5月11日的新西兰惠灵顿的《晚间邮报》(TheEveningPost)报道说:“顾博士的演讲以演奏中国民歌结束,他用笛子吹奏的这些精选的中国民间旋律吸引了全场听众。他是竖着吹笛,而不是横着吹笛。他解释说,中国的情歌描述的是婚后的爱情,其中一首题为《致我非常美丽的妻子》(《思美人》)引起了观众的一致赞赏。”[58]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报》(TheUbyssey)1934年3月3日也报道说:“演讲之后,顾博士用笛(箫)演奏中国民歌。歌曲选自广东、上海、山东、北京等地的民间曲调。”[59]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俄亥俄卫斯理报》(TheOhioWesleyanTranscript)1934年11月2日的报道更详细,除了提及“演讲结束后,顾博士用他的箫演奏了几首中国旋律”外,还写到“他解释说,这支箫的价格还不到我们的一毛钱(adime),由上有六个孔的竹管制成。简短的节目包括一首中国民间舞曲,一首名为《十杯酒》(《叹十声》)的哀歌,还有一首情歌《中秋闺怨》”。[60]久而久之,聆听顾子仁吹箫成了听众期待的一部分,报刊有关顾氏的讲演大都会提到“顾博士随时携带有一根‘魔杖’——中国竹箫”[61]。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生期刊《突出》(Salient)1941年6月18日的报道中就提到:“大概全场听众都对那个问顾博士是否带了他的箫来的人表示感谢。”[62]
三、巡游世界各地演示中国民间音乐
顾子仁最早在海外展示他的吹箫技艺应是在1920年7月的一天,地点是英格兰德比郡(Derbyshire)斯旺威克(Swanwick)小镇,场合是世界学生基督教运动同盟会会议上。当时在场的英国学生、基督教运动领袖何明华(RonaldOwnHall,1895—1975)注意到一个不寻常的中国男子。此男子“穿着一套根本不适合他苗条身材的西装”,但是当他开口讲话时,那流利、优雅的英语像施了魔咒一样让在场的学生们如痴如醉。后来,在休息的时候,此人又从袖中掏出一管竹箫,站在楼梯上,吹奏了一首名为《紫竹调》的中国摇篮曲。这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旋律和他的发言一样,以其简洁之美吸引并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一曲奏罢,掌声雷动”,此人就是顾子仁。顾氏的演讲和箫技给时在牛津大学读书的何明华留下的记忆之深,使他三十年后在为顾氏作传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仍有往事“历历在目”之感,顾氏演奏的《紫竹调》仍在他的耳边萦绕。[63]当时参会的一个美国学生代表在十多年后也回忆道:
顾子仁来访的消息让笔者想起了十多年前第一次目睹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中国学者时的情形……。这次活动是学生基督教运动的年度夏季会议。会议在一个大马戏团帐篷里举行,作者清楚地记得这位东方代表的个人魅力和精神力量给笔者留下的深刻印象。晚上,有“唱歌”活动(我们可以称之为“大学歌曲”),顾先生应邀用长箫吹奏了几曲,他的演奏赢得的全场听众的同声喝彩,其掌声之大,整个帐篷都几乎被震塌了。[64]
1928年,顾子仁升任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副会长后,开始频繁地为同盟会到全球各地巡访讲演。他《中国民歌》中的曲目也随着他的足迹被传扬到了世界各地,并进入到了欧洲、大洋洲和北美的许多城市和大学、中学校园。仅在他1929年一年旅行的行程中,就至少包括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雪城大学(SyracuseUniversity)、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University)、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College)和丹佛大学(TheUniversityofDenver)。[65]
除了在演讲前后吹奏中国民间乐曲外,顾子仁自1920年代后期起还利用到国外演讲和参加会议的机会抽空隙在当地举办洞箫独奏会。如1929年初在伦敦参会和演讲期间,他就应英国广播电台(TheBritishBroadcastingCooperation)的邀请,以“顾子仁中国箫独奏会”(见图5)为题录制了一台节目,他演奏的“七首曲目包括古典的祭孔乐曲《孔庙大成乐章》和民间广泛流传的每个母亲都会对她的孩子吟唱的最简单的摇篮曲《紫竹调》”,于同年3月18日10:35在伦敦播出。[66]

顾子仁在亚洲国家也曾举办过电台音乐会。如1940年12月《印度听众》(TheIndian Listener)就刊登过“中国印度亲善代表团团长顾子仁博士演唱中国民歌,并于11月在勒克瑙和拉合尔电台发表演讲”的消息(见图6)。[68]

顾子仁的箫乐(偶尔也演唱民歌小调)展示虽然大多是针对欧美、澳大利亚、新西兰西人听众的,但他偶尔也为海外的华人社团演奏。如1931年2月他应澳大利亚多所大学邀请讲演路过新加坡时,也曾为当地的华人社团及学校举办过演奏会。[70]1931年2月21日的《南洋商报》(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全国性中文报)就以《顾子仁博士在巡回俱乐部吹芦笛解说东西方音乐之异同》为题,对其2月20日举办的讲座音乐会有以下详细报道:
昨日巡回俱乐部周餐会中,特请新近由华南京之顾子仁博士演讲。顾博士于未讲述之前,先拟就两讲题。一为中国音乐(奏芦笛),二为中国问题,任会中人择其一,顾博士发言后,该会主席拉打氏提议请讲中国音乐,会员附和者极众,顾博士遂开始大谈其中国音乐。顾博士首称,“两年前当余赴英途中,在海轮上与同船旅客谈中国音乐,某旅客答谓,‘中国音乐好像将九只狸奴放在一布袋内,由一人坐在布袋上重压,而发出的叫声。’所幸余当时携有芦笛一管,余遂奏一曲中国爱情曲以说服之。”
顾博士继谓,任何一国家,其音乐居半为发泄人之心胸与情感者,有时于歌曲中亦能寻味之,不幸关于诸此种歌曲,在中国无记载可考,仅系耳传,博士曾耗费若干时光,由中国各省收集民间歌曲,并编成一本歌曲选。当博士研究中国民间歌曲时,发现若干颇有兴趣之歌谣,且博士以为中国南北两方,亦有互异之点,正如南北两方人民之风俗与人情,博士自身为南方人,故其身躯矮小,轻飘,举动甚灵活,中国北部人民则不然,身体粗大而性格老诚,中国音乐亦然南方者富幽扬嬝嬝之音,北方则含伟壮气魄。博士言毕随取出芦笛一支,以示众人,并谓该笛在上海仅以一角五分之代价,即可获得之,说毕博士以笛就唇,先奏南曲水仙花一调,后复奏北方吉林曲一。[71]
除了演示中国民间音乐的地域区别外,顾子仁在讲演中也常提及音乐的“东西互异”:
至论及中西之情歌有两种特性,与欧西情歌迥异者,博士先指述一点称,“在欧西各国,其情歌每每在婚姻未举行之前,但在中国则不然,情歌往往发现于既婚之后,盖中国男女,因旧礼教之束缚,于成婚之后,始敢言爱情,此即与西方迥异之点,(此时听众大笑不已),当然,此乃东西方社会风尚如此,在以往之中国青年男女,欲在未婚前,男女谈爱情,系不可能者,东西情歌另一不同之点为何,姑举一例言之,中国已婚妇女之情在思远征之夫婿,尤其在冬季为多,诸如歌曲中之词句。‘我想你始着了寒罢,晚上有谁为你铺褥展被?’‘余想在西方之妇女,颇少如是想念者,但在中国居半为夫妇间之相思。’”博士复奏一曲,名“可爱的人儿”系中国八九百年前之歌曲。
博士继称,中西音乐之另一不同之趣点,即中乐将终时,其声袅袅不绝,声虽断,而有令人感觉未断之情形,盖其终时,其尾声缓缓然而逝,博士曾奏中国民间最流行之“十杯酒”,为一悲伤之曲,普通约出诸被卖奴仆或妓女者之口,另一曲名为“十叹”,该两曲之每一杯酒或每一叹,均诉出歌者所受之痛苦。
上述者为悲伤之曲,中国尚有一种调戏或打趣之歌曲,诸如“凤阳花鼓”即其一,是种歌居半为卖曲者男女孩。在街坊上歌唱者,(按:该歌曲于中国舞台上亦常见之),歌时以击花鼓为击拍,两支细木棒击鼓面,作响趣之声,演扮者一男一女,彼此互相调戏,如夫妇般调笑口吻。博士最后演述中国之儿童睡歌,名为“紫竹”,当博士未将笛就唇吹奏该曲时,笑语听众谓“诸君闻后,将回家睡眠,(哄堂大笑)或者助诸君作一午睡”。博士并将睡歌之词曲背诵如下:词句简单而又富引诱性。
紫竹的笋——
当作笛儿送给你、笛儿接着唇、
唇儿依着笛、
奏一曲新的歌儿
小宝宝,已知怎样吹。
当博士在群众欢笑声中,缓缓坐下时,复谓:“我希望此一曲睡歌,诱迷得猫儿不在地板上跑,蹲在一角睡去了。”[72]
以上已经提到,顾子仁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欧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学进行讲演前后,一般都会吹箫来引发听众的兴趣,并像以上报道一样简单介绍中国传统和民间音乐。但他有时也会单独就中国民间音乐举办讲座。如1937年4月8日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的学生杂志《愿它运用绽放》(SemperFloreat)就刊有“4月15日下午1∶15顾子仁博士‘中国文化’竹笛独奏会”(“ChineseCulture”BambooFluteRecital)的讲座预告(见图7)。[73]

1931年4月14日的《悉尼先驱报》(SydneyMorningHerald)也刊登有以下顾子仁4月13日在悉尼大学会堂举办“中国民歌讲座”(ChineseFolkSongs.Dr.Koo’sLecture)的报道(见图8)。[75]1946年12月顾子仁还在加拿大温尼伯市曼尼托巴大学音乐学院举办过“中国民间音乐”讲座。[76]

除了举办独奏会外,顾子仁也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展示他的吹箫技艺。如1939年他就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上为参会的世界各国学生代表演奏箫曲(见图9)。[78]顾子仁的这些音乐活动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世纪后,仍有听众记忆犹新。曾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世界学生运动领袖的佛兰克·恩格尔(Rev.FrankG.Engel)在其1994年出版的《生活在世界共同体中》一书中,在第一章就专列有“顾子仁博士的贡献”一节,其中提到顾子仁“在与大型公众会议相比不是十分正式的聚会上他总会拿出他的中国竹箫,演奏中国民间音乐。他也会谈到古老的民歌,甚至教我们唱其中的一些”[79]。

四、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文化
谢扶雅说:“子仁于1947年,自北平挈眷移居新大陆。”[80]此说似乎有误。事实上,顾子仁是于1945年春就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来到美国参加联合国4月25日至6月26日举办的旧金山会议的。[82]会后,顾子仁本来计划继续留在美国“约六个月”,以便到南美和欧洲各大学及各种社团进行演讲。[83]事实上,顾子仁此次的南北美及欧洲世界巡回演讲远超过计划中的六个月,从1945年5月一直持续到1947年1月,时间长达近二十个月。[84]
1947年,年满六十岁的顾子仁从“供职历二十二寒暑”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退休,[85]但荣休后,“即为美国各机关团体所争聘,终膺受爱荷华州立大学之招,于1948年秋季,在该大学宗教学院,开‘中国文化’课程”[86]。关于顾氏在美任教的信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学院(AlleghenyCollege)校报提供的信息最详。据该报1949年12月15日的报道,“在1949—1950年的第二学期,顾博士将在佛罗里达大学任教。去年(即1948—1949第一学期),他是爱荷华大学的客座教授。此后,爱荷华大学再次任命他为东方学教授”。该报道还提到顾子仁历年来所获得的荣誉学位:“顾博士拥有凯尼恩学院(KenyonCollege)的博士学位和全国多所学院和大学的荣誉学位,包括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University)、丹佛大学以及刘易斯和克拉克学院(LewisandClarkCollege)的法学博士学位。”[87]爱荷华州立大学《爱荷华人日报》(TheDailyIowan)也在1950年10月3日的报道中,以“顾教授任爱荷华大学新设立的东方学研究系主任”为题,宣布了1950年秋,顾子仁再度受聘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担任远东研究专任教授的消息(见图10)[88]。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官方出版物《爱荷华州立大学公报》及《爱荷华大学宗教学院史》也提及顾子仁在该校的就职过程及所教授课程。[89]
在爱荷华州立大学东方研究系任教期间,顾子仁除了编写教材《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教学大纲》[90]外,最重要的是将其《民间音乐》一书更新再版。[91]关于此版《民间音乐》,谢扶雅提到:

1950年,在美国翻印他所心爱的《民间音乐》一书。不过为了时地的变迁,和不同的读者,所以他将原版本略予调整改订,将那专为当年中国学生爱国运动而作的几首新词,改转过来,而恢复保存原来的词句;同时又扩充原有的二十五首为三十三首,重新写一自序,印入了他亲笔的签名,表显他那种潇洒的风趣,与封面版画——中国所特有而美所不产的“竹”相配合。这改定本还加了一幅中国特出的天才诗人李白(公元701—762)的画像,作为扉页。子仁是有意要用这位潇洒旷逸的诗仙去箴砭和纠正美国过度紧张而带铜臭的工商业社会文明呀。新添入的八曲之中,有两曲只存了曲名(《渔翁乐》与《风入松》),而佚失其词句,相见这种曲子也确代表了中国民族性的风格,泱泱乎跟工商业社会所产出的歌曲大不相同,所以子仁也单把它们的谱不忍割爱地印了进去。[93]
顾子仁在爱荷华州立大学任教的期间,曾于1953年春季学期重回远东考察西太平洋的新情势,也曾踏足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到香港时,其老友时任香港圣公会教区主教的何明华还想请其出任空缺的崇基学院院长之职。但顾氏以“倦于教育行政而作恳辞”[94]。此期他还和谢扶雅约定“共同采选中国先贤佳训及历史上有益世道人心的隽永故事,把它英译出来,以药西方工业社会功利主义的偏弊”[95]。可惜此一设想因顾氏“不久[1959年冬天]即患部分脑溢血,神志半告丧失……未能偿其所愿”[96]。
在爱荷华州立大学东方研究系主任一职上,顾子仁一直工作到1955年夏天。当时的顾子仁已年满六十八岁,按照该校的规定,必须“强迫退休”,但毕竟“已为爱大奠定了远东文化研究的基础”。顾子仁从爱荷华州立大学退休后,仍没有放下教鞭,随即就又应美国的另外两所大学之邀,分别在巴克卫大学(1955—1956)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1956—1957)任教一年,直到1957年七十周岁时才正式离开教职。但他退而不休,仍不时到各地演讲,[97]直到1959年冬天,他在应邀到佛罗里达州演讲时,突发脑溢血昏倒在讲台上为止。[98]晚年的顾子仁与夫人朱琪贞(圣公会名牧朱友渔主教之妹)和子女居于德拉华州(DelawareState)的威明顿镇(Wilmington),1971年11月29日,顾子仁在克利扶伦城其次女家中去世,享年84岁。[99]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