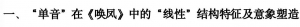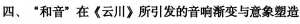作曲家 秦文琛
2023年5月22日,作曲家秦文琛的协奏曲专场作为北京现代音乐节二十华诞的开幕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成功举行。这四部作品——从唢呐协奏曲《唤凤》(1996/2010)、大提琴协奏曲《黎明》(2008)、琵琶与弦乐队《行空》(2012)到笙协奏曲《云川》(2017),不仅体现了秦文琛近二十年对协奏曲体裁创作的持续自我突破,也体现了他长期对艺术规格的坚守和对直觉与理念高度统一原则的遵循。当晚音乐会由指挥家俞峰携唢呐演奏家张倩渊、大提琴演奏家莫漠、琵琶演奏家兰维薇、笙演奏家郑杨以及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以严谨的职业态度和高艺术水准的精彩呈现,刷新了当晚观众对当代音乐作品的认知与理解。演出以其精准性、生动性和深刻性为观众带来更深入思考的同时,也让人对中国未来的创作,职业乐团的发展、中国当代音乐在国际的传播、乃至对中国当代音乐史的书写增加了期许。因对自然的崇敬和对世界丰富性的感悟,秦文琛在音乐中塑造了非简化之美,那是从感性流淌出来的音响组织形态,是作曲家对瞬间直觉敏锐的捕捉和耗费心力的有序书写。作曲家将从生活、自然规律中的发现释放在艺术表达空间的同时,也已悄然跨越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二元边界。所以,对于秦文琛音乐广度和深度的理解,除了对其理性的创作技法进行分析与归纳外,还需要我们具有接近作曲家那样的感性智慧,来探寻其真情的根源。
图:2023年5月22日国家大剧院演出现场
创作之源
一、象征符号
秦文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鄂尔多斯草原。在他的笔下,处处流露着童年生活的印记。“童年所有的乐趣都来自自然。” [注1]捕捉四季气味的变化,好奇花虫鸟兽的习性,喜悦春天燕子啾啾鸣唱,悲凉大雁南飞的远影……而与童年快乐始终相伴的还有牧羊时的孤独感。[注2] 孤独,使音乐自然而然地走进秦文琛童年的生活,成为他的精神寄托,并成就了他之后真诚、内省、质朴的音乐表达。同时,孤独也促成秦文琛在童年时独立思考的习惯——独自在草原上观云望月,掌握天气时时变幻;独自观察太阳,计算时间和方向;独自行走,聆听自己的呼吸和脉搏;直至他独自承受走出地域的背负,成就所追寻的艺术道路。所以,“孤独” 赋予作曲家一种视角或气质,它常常映射在 “行走” “脉搏” “永恒” “向往” “天空” “云朵”“鸟鸣” “太阳” “地平线” 这些属于秦文琛音乐语言系统的象征符号中,不断追忆和重温童年生活那纯净和美好,更体现了他从自然中获得的一种精神——高远的意境、宏大的气势、充满生命力的律动,表达着他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命的关切。
二、美学观念
秦文琛从自然中获得创作感悟的同时,也从中国古典艺术——(宋、元时期)山水画和(刘长卿、李贺等人的)诗作中领悟到自然精神的艺术表达境界,“自然中包含着所有艺术的法则”。[注3] “声音应趋向自然原理,遵守自身逻辑关系展开。” [注4] 在他的音乐中,整体结构和局部呼吸经常按照 “能量积聚—释放” 这样一种符合自然动向的规律布局,并在其中自如调用对比与统一关系,让性质差异较大的形象要素——直与曲、长与短、浓与淡、疏与密、明与暗、动与静、实与虚——同整体各要素之间组成合理秩序,“凭艺术借自然,却也超脱自然。” [注5] 由此,将技术化用于精神内涵和艺术格调之中。
三、主要思维
线性结构存在于自然与民间音乐中。对线性艺术的美学追求,是中国古典艺术——音乐、书法、绘画这些不同门类之间的共性。线性结构是秦文琛作品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近二十年来,一直在研究 “线” 的结构和产生本源,“我把乐曲整体的音乐形态最终归结为一条‘线’,这条‘线’可以最直观地体现结构的平衡”。[注6] 由此推断,“线”在时间上可以压缩成 “点”,在空间上可以扩展为“面”,他的 “点” “线” “面” 在作品中体现为 “单音” “宽线条” [注7] 和 “音响” 等形态。对于上述技法的使用,作曲家尤为强调“中心素材”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个世界从微观到宏观都有一个中心作为内在的凝聚力,而 “单音” 技法就是作品中心凝聚力最重要的体现之一。秦文琛对于 “单音” 的使用,从听觉出发,遵从音响运动过程中的必然逻辑关系。他通过对 “中心素材” 腔化、装饰,并对其在音色、音域、力度、节奏、速度等方面变化和组合,从高维度建立起东、西方文化背景下共生现象的交集,并创建了属于个人创作美学观下的语言系统,由此扩展了技法的表达内涵和表现意义。“点” “线” “面”不仅是塑造音乐意象的主要元素,也是本场音乐会四首作品中独奏乐器的表现特征。本文将通过四部作品的分析,来理解 “点” “线” “面” 作为 “中心素材” 的使用和其构成声音自然趋向的逻辑,探寻作曲家塑造音乐意象背后的深意和情怀。
创作之流
《唤凤》(1996)创作于秦文琛留学德国之前。作曲家在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已建立深层认知,而非流于表象,并且找到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径,在表现内容与整体结构、局部细节之间达到了高度的平衡。在这首作品中,可以看到作曲家将与少数民族音乐同频的性情转化为一种气质书写到音乐中,由此在当代音乐语境中凸显出个人创作风格。
(一)主题意象内涵
凤凰不流尘俗,孤傲超然,在通向永恒的道路上,注定要承受碌碌众生难以承受的一切。郭沫若在一百多年前将古埃及神话与中国传统凤凰形象相结合,构成了一个在烈火中复活的、永生的、翱翔的凤凰形象。它出现在中国近代艺术作品的表现题材中,将现实的悲观情绪转化为精神的永恒,平衡了痛苦与喜悦,进入了深刻的艺术思想境界。在《唤凤》中,唢呐独奏作为“凤凰”这一角色,引领乐队塑造了雏凤苏醒、日升东方、展翅啼鸣、火中凤凰、凤凰涅槃、火鸟重生的艺术形象。作曲家将这样一种立意和表现内涵与艺术形象塑造手法相匹配,使唢呐从民间音乐的功能、内涵、角色标签中获得重生,其艺术的深刻性唤起了那些抱有不断求索、寻求超越自我这样一种心路历程的听众的共鸣。
(二)主题意象塑造手段
1. 线性结构特征
在《唤凤》中,唢呐独奏的线条思维与中国传统音乐有着深层的关联,作曲家将民间器乐曲中通过丰富的演奏法、节奏、板式的变换对骨干音进行装饰的思维发挥到极致,形成了秦文琛的 “单音” 技法。秦文琛的 “单音” 与塞尔西的 “单一音” 、尹伊桑的 “主要音” 是源于不同地域文化滋养下,具有近似音乐形态的表达。秦文琛对 “单音” 技法的使用主要源于内蒙古潮尔的多声部音乐。“潮尔的音色深沉、含蓄又富于微妙的变化,蒙古人听潮尔,听的是感觉与韵味,是音符之外的东西……每当潮尔声响起,他们彷佛听到了时间河水逆向流动的声音,这是一个文化内部的人们共同分享的听觉体验与文化‘秘密’ ”。[注8] 所以,潮尔音乐赋予 “单音” 不一样的音乐气质。此外,秦文琛的“单音”是涵盖形态更为广泛且在不同作品中都会发生变化的开放系统,它的变化经常与其他要素化合出新的形态而模糊了“单音”技法的界限,从而使研读者在与“单音”相关的千变万化的形态中难以分类划分。作曲家对包括“宽线条”在内的使用思维亦复如此。“单音” 技法在《唤凤》中,既是音乐结构的重要支点,又是构建乐队音响结构的基础,它成为作品统一性的重要元素。作曲家以“单音”为中心,派生出音列和音组,发展出具有速率、板式变化的线性结构、音响结构和音型节奏。其中,线性结构是作曲家以形写神的主要笔法。在唢呐独奏部分中,“单音”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将“单音”进行腔化装饰,并在句式内部的律动上呈现从渐快到渐慢的特征;将“单音”扩展为五声音列作陈述语句;将不同调式的五声音列合并在一条线性结构中形成张力,再回归到具有结构意义的“单音”,等等。在不同的结构中,诸上线条形态的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在不同段落板式变化的加持下,通过演奏法或在不同调域对诸上线条进行偏移处理,使整部作品的气息、张力形成与题材意象——鸟鸣、展翅、焦灼、苦痛、升华——同样富有戏剧性的表达。
2. 音响结构特征
作曲家常常用潮尔的多声部音乐思维和其符合基音与泛音的声学结构原理,将“单音”转化为乐队的立体化音响,以良好的共振来展现音乐恢弘的气势。比如:排练号4,中提琴和大提琴作为踏板音,接过唢呐独奏的“单音”D,衬托着木管组、颤音琴、小提琴奏出D音引发的音调(d、c、a、g)和干扰音(#f、#g、#c、b),由此形成长短不一的线条。其颤动的、弥漫的音响效果时散时聚,在散板段落中形成能量积聚的过程。其生动性使人联想到地平线上群鸟将要起飞时的姿态和鸣叫,其音响姿态从自然画面,到民间音乐表演特征,再到声学原理,多维度地将自然界的美学规律映射在听者的记忆空间,唤起多重联觉而超越了具象。
谱例1《唤凤》排练号4开始部分的缩谱
这一写法在排练号23处进行了音响变奏,即:将清晰和模糊的音响在高、低音域进行对调,形成腔化的低频(大提琴和定音鼓在低音用往复滑奏的音响作踏板音),衬托唢呐独奏(以b2为中心的吐音)在高频的清晰性,此处的用法可谓四两拨千斤,寥寥数笔就将唢呐独奏处于危机四伏之境地。以排练号4作为音响展开的基础,其变奏几乎贯穿全曲。除了“单音” 转化为音响形态之外,最不能忽略且独具性格特征的还有将 “单音” 进行音型节奏化的使用,它也是这首作品与另外三首协奏曲最为不同的性格特征之处。
3. 音型节奏特征
作曲家在这首作品的能量积聚—释放过程中,尤为强调在两种形态之间加入性格鲜明的节奏型,形成焦点节奏。能量积聚—焦点节奏—释放这样一种音响逻辑贯穿于作品的整体与局部结构中。每一次对焦点节奏的处理都会对情绪有进一步的推进。处于不同结构的焦点节奏特征对整体结构的律动、层次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在呈示段,作曲家将排练号4进行分层处理所获得的弥漫音响效果逐渐累积到排练号5的焦点节奏——管乐组齐奏出由D音主导的 “单一音响”——“呼唤” 主题上,在呈示段开篇就掀起一个起伏,之后,音乐情绪通过“单一音响”逐渐回落到弦乐 “单音” D上;而排练号9处,乐队则用音块打断了积聚能量的织体,音乐突然转换形象,以“上板”来形成焦点节奏,与唢呐独奏形成“紧打慢唱”的律动关系,音乐的释放被板式节奏阻碍并替代,在中间段落形成戏剧性的推动;到了排练号13处,乐队全奏跌落到弦乐群的焦点节奏上,弦乐群用齐奏律动阻碍了能量积聚过程,在音场上与前面乐队分层的动态织体形成力量收缩,同时为后面乐队进入更加复杂的能量积聚过程提供缓冲,形成音乐气息的曲折性和音响效果的戏剧性,为全曲高潮的焦点节奏(第四段,排练号15—25)做了充分准备。第四段处于全曲的黄金分割点,作曲家巧妙地将具有华彩性质的唢呐独奏技巧(打指、花舌、回滑音、吐音、循环呼吸等)在该段落分为三个阶段层层递进,在不同乐器组节奏音型的烘托下,将听众带入凤凰在火中焦灼不安、群鸟在空中盘旋啼鸣的绚烂场景,为全曲的高潮焦点节奏积聚了能量,直到由木管、铜管、弦乐在三个八度以b为 “单音” 的齐奏与打击乐组粗粝地爆发出 “掀雷揭电、气腾日月的壮观景象,” [注9] 形成全曲的高潮,此处焦点节奏将苦痛、毁灭升华到壮丽的境界。作为高潮的释放,作曲家将第五段(排练号26—28)的 “笔法” 从“画功” 转为 “化功”,大道至简,将技术化于无形,从弦乐组奏出深沉而悠缓的音调,仿佛来自古老的歌,它与唢呐用颤音、飞指和破功音所构成的线条构成情境对位,作曲家对挣扎、颤抖、哀鸣和绝望那客观而又充满人情味的表达,让听者为其真实性而动容、潸然。“单音”不仅在《唤凤》的结构形式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艺术表达上幻化为具有精神指引的象征符号,使唢呐这件民间乐器的表现力提升到艺术音乐的表达境界。
《黎明》所表达的内涵与中国诗人海子的诗作互为映照,诗中 “天马、远方、太阳、天空、大海、飞翔” 等意象在音乐中的投射,体现了作曲家此时创作扎根大地的同时,对深远的精神境界也有所追求。作曲家运用线条的巧思与音响的抽象性表达,为听众提供了联觉空间。三个乐章的音乐性格、速度、音响空间布局、独奏与乐队的关系等,与三首诗作的标题 “黎明” “起风了” “火焰” 同步,呈现出递进式特征。第三乐章内部结构延续并充分运用递进思维,将第一乐章埋下伏笔的 “音块旋律”(纵向声部构成的音块,以同步节奏快速地在横向声部平行进行)作为第三乐章的核心素材,在音乐逐步扩展中,“音块旋律” 的规模与诗中意象——“像一片升向天空的大海,像狂放的天马,朝着河流飞翔” 高度契合。
这首作品对“四音列”的使用别具匠心。这个“四音列”(C、D、E、A)具有五声性,它来自大提琴空弦与内蒙古民歌《褐色的鹰》骨干音的巧妙结合,其中可以找到地域特征,但写法却不被地域局限。这首作品的 “四音列” 接替 “单音” 成为中心结构力。对于音列紧张度的处理,作曲家以五声调式为核心,扩展出若干音列或音阶,根据音响紧张度的变化来调配音高密度。
下面我们从三个乐章中 “四音列” 在独奏大提琴上的典型用法来看其与乐队之间关系的处理。
(一)“四音列”在独奏大提琴的多声线条形态
第一乐章对 “四音列” 构建线条的处理方法从引子(第1-23小节)的思维窥斑见豹。第1-8小节以 “四音列” 为中心元素,形成音响基色。作曲家充分利用大提琴独奏的空弦,将 “四音列” 中的三个音(C、d、a)用竖琴的 “点” 激发出来,在大提琴不同八度形成 “线” ,塑造了具有空间感的多声形态。这种多声形态升维了《唤凤》中 “单音” 在乐队中的使用,即 “四音列” 在不同音域以不同音色出现,同时它们分别被泛音形态的B 、#F 和夹杂在旋律中的be所装饰,形成远、近空间的切换和更为深情的表达。尤其对D音的运用很有意思,作曲家将在G弦上演奏的d音通过滑奏、微分音偏移以及泛音音色颤音的处理,形成线条的色阶流变,并穿行在空弦C、d、a之间。其音乐沉缓而肃穆,具有仪式感,彷佛尘封已久的生命缓缓苏醒并破壁生长。
谱例2 第1-8小节
在后续的发展中夹杂在“四音列”中的b、g、#f(第9-15小节),既是丰富核心音列的韵味存在,又是巧妙出自大提琴相邻把位的自然泛音。这种源自马头琴的演奏思维在作品中出现的那样自然,似偶然出神飘走的乐思,而正是这种恰到好处的偶然性,才使艺术逻辑中闪现出最为可贵的火花,但它们又像空中的风筝,飞的再远都无法挣脱核心音列的牵引。
(二)不同调式“四音列”交织成线在独奏大提琴的用法
在第二乐章,作曲家将不同调式的 “四音列” 或 “三音列” 交织在一起,形成线条的紧张度,并用装饰、填充、减缩、扩大、移位等手法对排在句首的不同调式的核心音列进行变形。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牧歌与长调特征对独奏大提琴线条的影响,其形态在音域间高低起伏,节奏疏密变化频繁,配合强力度的演奏,音乐流露出激动和不安。
对于乐队与独奏的关系,如果说第一乐章将不同音色组按起承转合的结构布局来衬托独奏大提琴的话,那么第二乐章乐器组音色转换则更加频繁。这个乐章的两个主要音响形态均由“单音”引出(这些“单音”主要取自“四音列”):一是 “宽线条”,在乐章的开始,弦乐组先与独奏同音,然后瞬间扩散出多声部,形成若干近似独奏线条的不同步的模仿声部,它们伴随且推动着独奏的进行,仿佛是由独奏激发在不同空间的回响;二是 “音块” ,这个形态依然是由弦乐组与独奏同音奏出,但它的能量好似在节奏上将 “宽线条” 中必然和偶然出现的音高形成瞬间的凝聚,乐队的能量附加在独奏大提琴上,成就了大提琴的音势,并与不同乐器组形成竞奏(第26-34小节)。第二乐章以“宽线条” 和 “音块” 这两种主要织体形态的交替,构成音乐的展开,结合音色密度和音响频度,完成了积聚—释放的过程。
(三)利用大提琴空弦对“四音列”进行偏移处理
第三乐章在独奏大提琴上将一、二乐章织体的点与线、音色的虚与实以夸张的力度相结合,将核心音列用斐波拉契数列数控节奏,形成逐渐增长的姿态,最后利用空弦,将核心音列在八度音程中勾画线条偏移,构成动力,并与十六分音符的单线条交替出现,恰如诗中 “狂放” “飞翔” 的意象。
谱例3 第32-33小节,对大提琴独奏音程的偏移处理
该乐章乐队写法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在弦乐组塑造了独奏的多样回声形态(第1-4小节);二是乐队好似被独奏点燃的火焰,时而出现在独奏之后(第6-7小节),时而又与独奏局部形成交织(第15-21小节);三是充满力量感并快速行进的“音块旋律”(第5小节)。
谱例4 第110-113小节,乐队由“单音”进行到“音块旋律”的写法
这三种形态均有各自的发展轨迹,但音乐选择将“音块旋律”贯穿整个乐章,经过层层铺垫,直至“音块旋律”的气势越来越强烈,形成与独奏的竞奏,最后全体乐队积聚成排山倒海之势,独奏在越来越小的间隙亮相,最终融化在强大的乐队音响中与之完成合体,乐队助力大提琴到达无法企及之境。
作曲家在构建核心素材时不惜笔墨,但后续发展总有用之不竭、出其不意的办法。三个乐章是用同一个核心音列发展出三种不同的意象,但它们内在关系又相互勾连,整体呈现层层递进、张弛有致、一气呵成的率性表达。第一、二乐章的结尾均在音响空间上勾画了诗中“远方”的意蕴,对整体情绪的递进形成迂回、缓冲的效果。第一乐章尾声似从远方传来的对精神的指引,而第二乐章结尾则是走向远方的回溯、凝望、思索和再启程(见第86小节乐队大提琴声部“行走”音型),作曲家“不停地行走在气象万千的自然中,由此被赋予无数戏剧性的音响事件。” [注10]
这首作品以琵琶的“点”状音响为核心语素,通过“点”延展出“线”和“面”,三者以渐进变化或反差对比的方式形成多样音响形态,推动音乐的发展。其丰富的想象力以及与电子音乐相近的思维,将天空光韵的变换以音响的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了作曲家自如、自在、达观的精神境界。
(一)结构与素材逻辑关系
如果按琵琶织体形态来划分,其整体结构为并列三部曲式,次级结构则具有中国民间联缀多段体的特点,可分为六段。琵琶在每个段落的形态均基于核心音列的变奏,并且在每一个变奏中,织体形态从始至终都保持统一性。而弦乐队与琵琶的展开方式则不同,弦乐队塑造了三个主要音响体:
谱例5 谱例a、b、c分别取自第1、15、28-29小节
谱例5a是音响的呈示(具有夸张渐强力度的和弦交错);谱例5b是音响的发展(延续渐强力度,增加滑奏使其具有推动力);谱例5c是音响能量的回落(无音高、节奏对比的音色原地动荡,形成弥漫的音响效果)。从谱例5a到谱例5c并非音响的连续,但它体现了句式或段落之内,音响动能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与传统音乐起、开、合句式具有相似性。三个音响体在第一段依次出现,在之后的每个段落中,弦乐队的织体形态均由这三个音响体的变奏组成,也就是说,三个音响体通过各自幅度、篇幅、质地的变化,以及在音响体之间化合、衔接的重组,为每个段落的琵琶独奏塑造了不同的音场,二者间的展开思维形成了异步多重现象。其中不乏突然插入由琵琶转化到弦乐的“点”状音响语汇(第41、46小节),以及在《黎明》中象征“永恒”(第48-49小节)的形态,来打破三个音响体的逻辑关系,使音乐充满趋向自然的意味。
(二)改变琵琶定弦对空弦的使用
为了丰富和弦及泛音,作曲家将琵琶的定弦由A、d、e、a 改为B、d、e、a,并延续了《黎明》中对空弦的使用和五声性“四音列”的核心音高思维,但基于“四音列”的音响构成却与《黎明》很不同。《行空》一开始以自然泛音演奏法在四根弦的不同音位(将左手手指与品/相平行放置,在第三、第五、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十四泛音位置虚按琴弦)奏出具有不同色彩对比度的泛音和弦,这些泛音和弦快速地交织,形成了泛音音响群落,这些群落又被弦乐分声部延迟,塑造了琵琶的折射光音响。此外,作曲家还巧妙地运用空弦上的自然泛音,在琵琶上延续着“单音”思维,比如:以d为核心音,用B 弦上的大三度泛音(#d)装饰d弦上的八度泛音(d),在句尾通过渐慢、渐弱来释放乐句的能量;演奏d、e两根弦的大六度泛音(#f、#g)对a弦上的实音g进行偏移处理(第58-59小节),这个带有g音偏移的线条,为弦乐队近似光能衰减的音响的进入做了铺垫。
而对于琵琶实音的运用,空弦B、d小三度则是作曲家的乡音——鄂尔多斯民歌的核心元素,在琵琶横向线条中具有一定篇幅的展开,尤其在第二段(第31-49小节)和第六段(第118至结束)体现的尤为突出。可见,小三度在纵横向音高构建中对全曲结构力的重要性。另外,作品中还不乏将五度、七度(琵琶II和III空弦二度音程的转位)作为核心音程以不同的音响姿态进行展开的段落。作曲家将空弦为基础所构建的和音与音程细胞,充斥在作品的不同结构段落,形成统一与变化的关系。
(三)独奏与弦乐队的音响关系
1. 折射光(见谱例5a)
弦乐用实音(近码演奏)或泛音的拉奏与琵琶泛音扫弦以相同音高同步发声,并以夸张渐强的力度放大琵琶“点”状泛音和音的音响,如同琵琶激发了弦乐队的光源反应,弦乐的不同声部在舞台不同方位以不同音色、不同时值形成此起彼伏的折射光音响。
2. 流动光体
滑奏在秦文琛的作品中有着重要且多样的表现力。在《行空》中,作曲家在弦乐上运用大量滑奏及变形,作为作品核心形态之一,与琵琶一起呈现丰富的音响体,比如:第15-16小节,由琵琶泛音扫弦激发弦乐队的不同声部以不同步的滑奏呈现的音流,是一个具有推动力的音响。在后面的发展中,由滑奏构成的音响元素在弦乐队上变奏出流光溢彩(第23-26小节)、强大光流(第42-44小节)效果,给予了独奏能量。还有一种近似光能衰减的音响(第60-71小节),它仿佛将人讲话时 “叹息” “疑惑” 的语气在频段上作了调制,这个音响是在弦乐的柱式和弦音中,有选择地对部分音高作滑奏处理,分散了柱式和弦的能量,使之不能聚焦,它在琵琶那渐变且晃动的持续音背景的衬托下,彷佛是对久远信息的回放。而之后出现的微弱的散射光(第73-80小节),则是光能衰减之后能量进一步的释放,它将柱式和弦变为用弓杆抛弓和滑奏组合而成的短小线条,在不同声部形成错落感,作为背景似有似无地衬托琵琶在中低音区 “孤独的” 单线条的起伏。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光的扭曲(第85-106小节),这个音响是在弦乐队上,将具有滑音形态的三组 “宽线条” 作对位处理,其效果好似将合唱的每个声部进行扭曲,三组 “宽线条” 与琵琶的线性织体形成第二层面的音响对位。当这个音响具有一定篇幅时,仿佛将人带入幽暗无尽的、时间消逝的宇宙空间,我们在体验作曲家觉知的同时,也在感佩其丰富的想象力和与之高度契合的作曲技术。
3. 象征 “永恒” 的音响
在秦文琛的作品中,表现“永恒”最常见的织体是作曲家在限定的时长内,让演奏家按照记谱间距自由选择时值,从而形成出音点错落且无力度变化的静态之美,比如:《黎明》第二乐章C段(第69小节-结束)、《行空》的尾声(第200小节-结束)等。在《行空》中还有两个象征“永恒”并具有结构意义的素材:一是五度持续音,它在第一段(第1-30小节)、第三段(第50-72小节)、第六段(第118-199小节)以及尾声(第120-结束)均有出现,作为踏板音粘合不同音响;另一个是七声音阶(谱例5c),它在每个声部以五度音程呈现,纵向叠加成七声音阶的音响。可以说,七声音阶是由五度音程扩展而来。这个音响除了第197小节最后一次出现时,与琵琶摇指一同呈现缓缓升腾的明亮光线折射之外,在其他结构中,这个音响作为能量释放,常独立出现在句尾。
4. 闪烁光体
在秦文琛的作品中,经常会发现跨越要素、跨越范畴的转化思维,这是他对本质、对共性敏锐觉知的体现。在作品第41小节、第46-49小节,弦乐上“点”状泛音的演奏法由琵琶演奏法转化而来。该演奏法体现为自然泛音与人工泛音交错而形成的有控制偶然节奏的泛音群落,它衬托琵琶泛音的节奏从有序逐渐走向无序,塑造了光斑从积聚到释放的过程。这首作品从独奏与乐队的配合,到听众的听觉习惯,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笙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它在历史文献和民间音乐中常以合奏、领奏、伴奏的角色出现。在中国近代音乐史,笙的独奏作品数量逐渐增多,并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作为一种在音色上具有统一性、融合性,在功能上具有多声性、自由簧的乐器,被挖掘出更多的表现力和内涵。秦文琛在创作《云川》之前,已在《迭响》(2004)、《唤起记忆的声音I/II》(2006/2008)、《向远方——为中国乐器而作的30首室内乐》之《唤醒黎明》《日出》《冬》(2010/2011)等作品中建立起笙与中外乐器多种组合的写作经验和美学思考。但对于协奏曲的创作,笙在音色上的融合性反倒为写作增加了难度,加上其音域窄,指法无规律可循,不同音域的音程关系有差异等特征,使笙协奏曲的创作成为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谱例6 26簧传统笙的音高 [注11]
(一)创意及构思
对乐器构造及乐器法细致而全面的研究是秦文琛创作前的必备功课。他根据乐器的特性从新的角度升华了一直遵循的趋向自然的表达。他“使用音响展开的写法,更像一幅山水画,它遵循着声音自身的逻辑关系,趋向自然……” [注12] 我们从中既能听到“白云远送向青苍”的辽阔,也能感受到“山阔云低浅草连”的笼罩与宁静,在“山随云影转阴晴”的刹那,抒发着作曲家参悟自然山水的智慧,将笙的表达内涵推向物我同一、情景相即的境界,从高远的意象塑造折射出作曲家的心境,由此而展开一系列不为刻画之跡的音响设计,使笙与管弦乐队之间化合出相近的特质和气韵。其结束方式意味深长,笙演奏的七个和弦象征独行者远去的背影……作曲家将“孤烟飞广泽,一鸟向空山。” [注13] 的孤独交给音乐,将旷远的凝望留给听众。
(二)音高组织
对于音高布局,作曲家将笙的26个音作为基色,筛选出适合十个手指指法的和音组合,并将二度音程作为核心音高置于绝大多数和音中,在不同的结构位置,将不同数量与叠加密度的和音在不同音域布局,形成音响的渐变、突变或微变。二度作为和音的中心构架,又被作曲家运用在乐队的纵向音高关系中,对笙的和音进行补色(增加笙没有的音高)或调色(加入小二度或微分音与笙的个别音高形成拍音)或带入作曲家常用音列中,抑或将三者进行组合,以此改变笙的和音色彩。
谱例7 核心音列
这个核心音列的排列并无规律可循,音列以小三度开始,以大二度作为结束。笔者认为其特点与鄂尔多斯民歌核心音程和句式特征有密切的关联。根据笔者对作曲家的采访了解到,“小二度、微分音不仅是作为色彩差异的存在,它们在作品里经常代表了歌者(或演奏者)在不经意间表达出来的韵味。”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小二度在音列中的意义,它与作曲家经常使用的微分音、滑音在作品中的意图一致,同属于作曲家的乡音符号,它们是独属于作曲家的表达内涵特征。这个音列被作曲家运用于多部作品中,也许,这是作曲家对思乡情绪的含蓄、独特表达方式。小二度、微分音除了表现色彩、韵味,它还作为一种音响构成的重要元素被用在《云川》中,其具体形式体现为拍音。
(三)音响元素
作品引子(第1-2小节)的音响形态以拍音、特殊演奏法和打击乐音色三个主要元素构成。它们与点、线、面(音块)织体结合成具有《云川》特征性的音响形态,整部作品是基于引子材料的发展。
1. 拍音
拍音是指当两个频率十分接近,而且振幅也大体相似的声音同时发响时,引起振幅周期性的改变而形成的一种发音时强时弱的效果,亦称拍频。[注14] 作曲家在创作《地平线上的五首歌》时,从手风琴的发音中发现并偏爱上这种声学现象。“由于音区越低,各音间的频率差越小,产生拍音的可能性也就越多。” [注15] 所以,作曲家不仅在《云川》第2小节用拍音(由圆号、长号、大号在低音区奏出A和降B两音)制造音响效果,而且还将这种配器思维运用在高音区(两支短笛奏出的升3/4c和d音),力图使两极线条具有音响性。发生在两极音域的音响与中声部弦乐下行颤动的音块,以不同力度、不同进入时间、不同行进方向形成了瞬间动态音响,它在打击乐音色的笼罩下,将听众带入梵音空谷之境。在之后的发展中,拍音式配器在高、中、低音区也多有体现,它干扰、模糊了核心音高的属性,达到接近音响的意图。尤其在低音区,拍音式配器思维演变成音块或两个频率相近声部以滑奏的形态出现,并与偶尔出现的单音交替,间断性地贯穿于全曲,产生低音的音响流变,宛如远观黄河九曲的蜿蜒奔流。由拍音式配器思维延伸出音块的用法,在《黎明》中也多有体现,尤其是它在弦乐低音区被弱力度演奏时,其复杂的拍频已失去弦乐本身的音色特征,效果似大地从远处传来的阵阵的轰鸣声。
2. 特殊演奏法
特殊演奏法赋予音高独特的性质。在第1-2小节,弦乐对d、f核心音程进行小二度和微分音的填充,形成密集的音块,伴随着强压弓和震音的音块以下行滑奏的姿态,使这“一声叹息”参杂了些许内在而复杂的情感。震音、颤音、滑奏在音乐发展中被多样化的使用,使音高产生不确定性,形成一种动态的音响体,对推动音乐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由特殊演奏法形成的动态音响体的形式还有:巴托克拨弦;弓杆击弦;左手指震指板;木管自由复合音;铜管阻塞音等。这些音响体与打击乐的结合,幻化出新的动能。
3. 对打击乐的使用
第1-2小节,两位打击乐演奏者左手持钹,右手持钵,用钵在钹面的上侧来回击打,发出灿烂的声音,它象征着一种感召力量。打击乐和乐队构成的特殊音响贯穿全曲,不仅成为这部作品鲜明的特点,而且在音乐加速过程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音响结构逻辑
1. 音响渐变元素特征
作品整体结构依据音响形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第3-130小节)呈现了以笙的和音为主导的长音(A形态)到第二阶段(第131-336小节)断奏(B形态)的渐变。乐队与笙的音响关系相辅相成并具有独立的音响逻辑,即从第一阶段以乐音音响(A形态)为主导逐渐蜕变到第二阶段以噪音音响(B形态)为主导。笙与乐队的音响渐变绝非从A形态逐渐演变到B形态的简化过程,而是在原始音响A形态阶段中就隐含了B形态的元素。在发展过程中,B形态元素被逐渐蜕变成主导音响。
2. 音响渐变技法运用
在宏观音响结构趋势下,笙的音响句式关系如云的姿态充满起伏变换,其变化主要依靠和音的数量、排列法、演奏法、变化频率和速度等参数。尤其是演奏法中的指颤音、花舌、呼舌、历音、抹音等,它们在第一阶段赋予笙的长音由疏到密的律动频次,使笙在乐队音响中凝聚音色焦点,稳固主奏地位,逐步将音乐推向第二阶段的断奏。对于笙的断奏的推动,除了使其演奏法发生变化之外,主要依靠频繁地改变笙和音的节拍和重音,使其律动充满不稳定感,在穿行于多个不确定性的、非乐音的、有控制偶然的乐队音响变体时,形成了以笙的音色为核心的乐队音响布局。乐队音响句式逻辑的构建,与用分形 [注16] 原理绘制山川河流的复杂性相似,即对引子中的点、线、面构建而成的基本音响形态及其变形进行有选择的叠加,形成不同程度的音响密度,以乐器组之间音色多样化的调用,形成不同程度的对峙频度,在速度和打击乐节奏的加持下,配合笙的演奏法、和音密度共同形成推动力,在能量积聚—释放的过程中完成音响的渐变。
3. 音响渐变中的曲折性
在两个宏大的展开阶段,笙与乐队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其细节丰富而曲折,比如:乐队在声部空间上为笙作出让步,突出笙的主要角色地位,并点缀、装饰、强调笙的某些音,为其增添些许俏丽的色彩;乐队与笙融为一体,增加笙的织体、音高和音色的层次,使笙与乐队化合为一把超级乐器;抑或在笙穿梭于乐队的音响变体时,与乐队形成多样化的音响对位,等等。乐队音响如光和云的景象,变换无穷,几乎没有两处织体完全一致,其变化对笙的运动产生极大影响。加上秦式的象征符号——鸟鸣、行走、脉动以及《行空》《黎明》作品中特征素材巧妙地“客串”其中,或助力音响的推动,或短暂跳脱逻辑而形成对比,使整体音响在合理而流畅的起伏运动过程中充斥着不可预知性,其魅力恰如千形万象的自然景象。作曲家在笙与管弦乐队的音响上碰撞与延伸出无限的可能性,他调用丰富的手段在空间和时间上构建悠长气韵,绘制出独属于这部作品的音响画卷,来表现精神意趣。
结语
纵观秦文琛这四部协奏曲的创作,每一首都在音乐情感表达中,系统地注入了新视角、新思考。作曲家带给我们不同声景的时空感受的同时,通过将主观逐步融入到自然智慧中而实现对情感越来越抽象化的表达,不断地丰盈着艺术理想。当然,作曲家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一定充满了艰辛,除了对自我不断的突破,还要背负超越大众认知而常常带来的误解,超越演奏家的调性思维和演奏经验而承受的情绪反馈和背道而驰的音乐效果,由此造成作曲家可能失去对谱面与实际音响的客观判断,而动摇了最初的想法。所以,笔者理解秦文琛在采访和讲座中提到的“坚守”,主要是来自在时间中的等待,在现实的压力下,等待人们对当代艺术美学、观念的转变,能够倾听和尊重个性化的表达,进而在当代语境中形成创作者与观众精神层面的交流,而不是被同质化。这场音乐会能够代表中国近三十年来,致力于现代音乐推广的众多音乐家不断努力所带来的转变,在日积月累的活动中,使观众逐渐形成了对多元化艺术的包容和对优秀作品的判断。由此,在综合条件成熟的前提下,本场音乐会近乎完美的呈现实现了听众对秦文琛作品不同层面的理解。所以,没有艺术上的坚守,我们就不可能跟随秦文琛不同时期的音乐作品,进入到他那目不能及的疆界。在他塑造的客观、丰满而具有不确定因素的音响画面中,去感受更为自由和宽泛的意绪。
回溯秦文琛的童年生活到本科学生时代泡在图书馆饱读音乐史文献的经历,他很早就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发现自我,并建立自己的美学判断,不盲目追随任何流派,不断突破惯性表达。基于创作情感表达的需要,他从民间、自然、中西方传统和当代音乐中汲取养料,滋养己擅所长,即:用当代视角诠释中国民间音乐的形态、律动和韵味,在必然逻辑下涌现偶然因素灵性的火花;从中国书法、绘画、诗词中学会用自然中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来体现文人精神和风骨。他的自然观是与勋伯格阐述序列音乐在结构上同胚胎的拓扑概念(“所有的东西都是同一物,从根、茎到花”,“然而,同一形体却始终以新的面目出现,从这种重复中出现的是永恒的变化。”[注17])相一致却生化出不同的结果。同样,他的自然观也使其获得了频谱音乐、电子音乐必须通过客观实证才具有的声音认知。在秦文琛的笔下,他对声音的塑造跨越了实证的抽象性而更具人文精神,且“充满了中国的诗意特质。” [注18] 不仅如此,秦文琛用他独有的复杂声韵和音响效果,以新的可能性去丰富、扩大如同在调性音乐中音高要素所具有的那种中心性和张力关系,为当代音乐注入应有的生命力,从而与听众在人文精神和情感上取得共鸣。由此,他的美学观、自然观将听众引入他所坚守的艺术格调和他一直追寻的澄澈而崇高的精神境界。
这四部协奏曲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秦文琛近二十年音乐创作的发展轨迹。他的音乐是对于记忆和情怀不断的续写,在续写中不断的思考与追问,他的众多音乐作品已构建成一部宏大的诗篇,从中我们看到了作曲家独立思考的艺术人格,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艺术追求,在坚守艺术品味的情感表达中,不断探索与突破的艺术创造精神。秦文琛对中国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独特的表达和一系列成功作品在国内外重要的音乐活动中上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他也为中国当代后继的作曲家们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和启示。作为国际著名的音乐出版社Sikorski Musikverlag的签约作曲家,“秦文琛的例子表明,当代中国正在为世界艺术宝库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注19]
作者简介
朱琳,博士,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澳门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作曲与作曲理论学会理事,以及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理事。朱琳在创作道路上持续探索,不断推出新颖之作,这些作品涵盖了管弦乐、民族管弦乐以及室内乐等多种音乐形式。她的作品不仅在国内众多重要场合上演,而且在国际舞台的交流中也赢得了广泛赞誉,并且荣获了多项荣誉和奖项。
文章注释
[1] 秦文琛口述、袁梅执笔:《再高的云彩也有一把梯子》,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40页。
[2] 同注1,第78页。
[3] 周勤如 郭赟记录整理《与作曲家秦文琛谈音乐创作》,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15页。
[4] 本文作者对秦文琛的采访。
[5] 朱光潜:《诗的意象与情趣》,原载于《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1948年3月。
[6] 周勤如 郭赟记录整理《与作曲家秦文琛谈音乐创作》,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6页。
[7] “宽线条”是作曲家在诵经和民间音乐中发现的多声部现象。具体形态体现为:众多声部在大的方向上一致,只有演奏同一旋律时出现刻意设计的“不精确”造成大片错位的音响。
[8] 徐欣:《声音与历史——以声音感为中心的蒙古族乐器“潮尔”研究》,中国音乐学,2011年第4期,第37、38页。
[9] 李吉提:《雏凤声清——唢呐协奏曲〈唤凤〉赏析》,人民音乐,1997第8期,第9页。
[10] 李鹏程:《秦文琛在当代音乐周》,华音网2022-10-29。
[11] 作曲家根据创作的需要,用降b1音替换了传统笙的c2音。
[12] 解瑂:《乐自心中行天地——对话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家秦文琛》,中国艺术报,2018年3月21日。
[13] 引自唐代诗人刘长卿的诗作《使还至菱陂驿渡浉水作》。
[14] 杨立青:《管弦乐配器教程》上册,第6页,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年1月。
[15] 同上。
[16]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分形几何学由法国数学家曼德尔勃罗特在他的著作中被提出,其基本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局部与整体在形态、功能、信息、时间、空间等方面具有统计意义上的自相似性。分形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
[17] 杨立青:《乐思·乐风——杨立青文集》“管弦乐配器风格的历史演变概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第114页。
[18] 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终身作曲教授扎杰拉茨基·谢沃洛德·谢沃洛德维(Zaderatsky Vsevolod Vsevolodovich )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于2023年9月29日举办“秦文琛教授专场音乐会”后做出的评价。
[19]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