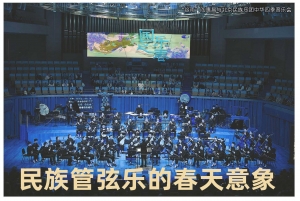2024年4月20日,正值谷雨时节的北京城开满了20蔷薇与月季,湿润舒适的春风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由北京演艺集团主办,北京民族乐团承办的国家大剧院第二届“国乐之春”系列音乐会——“谷雨”阎惠昌与北京民族乐团中华四季暨北京民族乐团2024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成功上演。本场音乐会由香港中乐团指挥家阎惠昌执棒,北京民族乐团演奏,特邀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赵太生联袂出演。“雨生百谷,万物逢时”,一位享誉世界乐坛的指挥,一个青春朝气技术精湛的民族乐团,几位顶级的表演者携多首老中青三代作曲家的代表作品,呈现民族管弦乐的春天意象。
一、音乐会掠影
本场音乐会以“谷雨”为主题,既是人民时令生活在音乐审美中的呼应,亦是对国乐发展成果的展示与期望。在以往的音乐审美体验中,每当提到以春天为主题的音乐作品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深入人心的西方作品,如贝多芬的小提琴《春天奏鸣曲》、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之“春”)、门德尔松无词歌中的《春之歌》、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等。本场音乐会上演了多首以“春”为主题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充分展现了创作者们用音乐语言表达着不同维度的生命情感体验。
民族管弦乐《大地之诗》
音乐会以《春颂》开场,该曲由香港中乐团委约,青年作曲家伍敬彬创作,最初以音乐短片的形式于2021年在网上首播。作曲家充分发挥传统锣鼓乐的丰富性及对节庆仪式的声音渲染作用,以完整的民族打击乐编制为基础贯穿全曲,营造节日氛围,乐曲由如春雷般的大小堂鼓组合引入,并在之后承接段落使用了十面锣与编钟,金属类乐器高频的点状特色成为听觉中“金声玉振”的音色记忆。北京民族乐团打击乐声部表现异常精彩,精准节拍框架里有着对弹性节奏的细腻处理,演奏中更是恰当地融入类似武术与舞蹈的肢体语言,将传统鼓乐的精气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描绘出中国人春节的声音景观。在旋律部分,作品运用了李焕之《春节序曲》的主题,以原样、模仿、变化的形式在不同声部分解与重塑,赋予此旋律新的精神面貌,似乎站在当代的春意盎然里回首往昔的春节印象。
第二首乐曲是彭修文于1987年创作的套曲《十二月》之《四月》,据阎惠昌介绍,选取此曲除了与音乐会主题契合之外,还表达其对恩师的追思,并以此铭记彭修文在民族管弦乐上做出的杰出贡献。彭修文为《四月》撰写的题记为“绿柳婆娑舞翩跹,百花盛开街头园。游人不识春将老,云淡风轻近午天。”乐曲以扬琴“反竹”技法奏出晶莹剔透的线性乐音开始,在乐队的铺垫中,笙、高胡、竹笛等乐器轮流演奏出优美的主题旋律,充分发挥了民族乐器的音色之美,以灵活的乐器配置探索民族管弦乐队自身的交响性特征,营造出生机勃勃、繁荣美好的四月意境。
第三首曲目《大地之诗》是李焕之创作的最后一首作品。1999年,在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中,收到一份没有署名的投稿,但凭着多年来指挥李焕之先生作品的经验,阎惠昌辨认出这熟悉的手迹,此时李焕之先生已经身患重病,仍惦记着支持民族管弦乐的创作和香港地区国乐的发展。全曲以传统奏鸣曲式写作,英雄式赞歌作为乐曲的主部主题,奠定其史诗般的气质;如歌般的副部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歌颂;再现部以打击乐勾勒出进行曲的节拍特征,展现出坚定而铿锵有力的精神风貌,那是作曲家坚韧不拔与不坠青云的意志,更是他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愿及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2000年3月中旬,阎惠昌指挥香港中乐团首演此曲,在听到实况录音的第二天,李焕之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①时隔25年,阎惠昌回到北京再次指挥这首乐曲,是对李焕之及民族管弦乐事业的传承。
上半场最后一首曲目陕北说书与乐队《刮大风》是王丹红创作的民族管弦乐组曲《永远的山丹丹》的第四乐章,取材于陕北说书曲牌《刮大风》。可以说,这部作品探索出一种新的民族交响乐体裁,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曲艺民族交响乐。作品没有将传统音乐作为色彩性片段的点缀式展现,而是完整地保留传统曲艺说唱形式,使之成为表演的主体与核心,巧妙地将陕北说书的方言化旋律、长短句的丰富节奏变化进行民族交响化处理,在更复杂的乐队编制中放大其民族化本体特征。同时,发挥管弦乐深层情感表达、意境营造的功能与特长,使两者充分地互融、互辅、互补,进而展现出陕北人民积极进取的生命态度与地域性人文精神。音乐会上,陕北说书表演者赵太生曾就职于北京民族乐团的前身北京歌舞剧院乐团,现任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在本次“回娘家”的演出中准确、生动地“扮演”了一位陕北说书艺人。
下半场第一首曲目是阎惠昌创作于1992年的大三弦协奏曲《傩》。“傩”是古代驱赶疫鬼的一种形式,作曲家以《周礼·夏官》记载的傩礼为创作灵感来源。中国民族管弦乐拥有丰富的民族乐器音色资源,作为指挥和作曲家,阎惠昌敏锐地对不同乐器在民族乐队中所具有的音乐表达能力进行多种可能性的探索。例如在本曲中,乐队里有三种对全曲有着至关重要的音色:其一,钹在弹性节奏中急促转渐慢的闷击演奏,类似川剧锣鼓中大钹的“大分家”的效果(川剧中用于战败后掩面而下或部分官员、将军等角色上场使用),在本曲中极好地营造出紧张而神秘的气氛。其二,特色乐器埙运用于多个音乐段落中,当乐队从各种宏大音响转为寂静之时,其呜呜咽咽、古朴幽深的音色描述神秘萧索的气氛。其三,赵太生演绎的三弦扮演了傩礼中祭司的角色,极大丰富了三弦的演奏技巧与音响表达方式,时而紧张凝噎,时而镇定流畅,时而激动热情,在驱疫除魔中表达人定胜天的精神。选择这首乐曲也是对人类终将战胜疫情的隐喻。
陕北说书与乐队《刮大风》,说书、三弦:赵太生
大三弦协奏曲《傩》,三弦:赵太生
女高音与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女高音:吴碧霞
指挥:阎惠昌
以传统乐曲创编的乐队作品是构成民族管弦乐“曲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柳尧章、郑觐文于20世纪20年代以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的《春江花月夜》即是此类作品的开山之作,此后,多位杰出的作曲家不断对这首琵琶曲进行叠写与创新,在传递古曲文化精神的同时,不断赋予其时代的新声。本场音乐会上演的花腔女高音与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由作曲家徐景新根据同名民族管弦乐填词改编而成,而当晚演出的版本由张博改编,此曲结合西洋声乐中的花腔技法,以现代性的艺术形式表达古典艺术中的文化意境。特邀歌唱家吴碧霞担任独唱,其表演既有西方声乐花腔华丽恢弘的气势,又有中国声乐细腻的旋律润腔和“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的美感,赋予传统文曲和中国诗词新的艺术特色。
最后一首曲目《十面埋伏》,是由香港中乐团于20世纪70年代委约刘文金和赵咏山改编的民族管弦乐。《十面埋伏》原是琵琶武套的代表曲目,琵琶以第三人称叙事的方式生动地描述了楚汉战争的故事,丰富高超的左右手技法及对战争场面激烈而恢弘的渲染,使其成为传统器乐曲中的经典之作。民族管弦乐版《十面埋伏》的交响性乐队配置提高了音乐表现的丰富性,在传统描述风格的基础上增加了情感的表达与戏剧性的对比与冲突,然而,相对于琵琶独奏中较为自由的弹性节奏,要做到不同声部整齐划一且保留其动态之神韵,对指挥及乐团而言均有着较高的要求。本场演出中指挥和乐团展现出的成熟控制力和游刃有余的技术高度,使其成为这部作品又一个经典的演奏版本。
此外,吴碧霞特别献唱由作曲家罗麦朔改编为民族管弦乐配器的古风歌曲《广寒宫》返场演奏了香港中乐团常演的1983年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插曲《世间始终你好》。两首脍炙人口的流行风歌曲展现了民族管弦乐与大众审美的结合及走进民众日常艺术生活的现状与无限可能性。
二、建构民族管弦乐的春天意象
中国民族管弦乐这一音乐体裁或多或少受到西方乐队模式的影响,也可视为“是西方化在中国音乐中的体现”②。然而,在乐器材质、演奏方法、声学特性、音乐文化传统、审美观念等方面,两者存在不小的差异。如何弥补民族管弦乐存在的不足,发挥自身的特色与优势,作曲家、指挥与乐团是最重要的实践者和创新主体,相互间经验的交流与碰撞是共同进步的有效途径,亦是本场音乐会成功建构民族管弦乐春天意象的重要因素。
音乐会中,不同年代的作曲家为我们呈现民族管弦乐经典作品和建构春天意象的三方面启示。第一,源自中国人生命情感体验中的艺术题材。作品中春节、谷雨、四月天、春江花月夜等元素,是中国人文化传统中认知春天和理解春天的方式,也是对春天最具符号性的情感体验。第二,丰厚的传统音乐文化土壤。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是民族管弦乐创作的重要源泉,传统音乐不同体裁、丰富的乐种与乐器及音乐素材成为创作中最宝贵的文化财富。第三,多元的现代管弦乐创作观念与技巧。民族管弦乐经历了移植传统、借鉴西方逐渐走向融合创新、多元并存的创作理念及创作技法。同样是关于春天的主题,本场音乐会中有《大地之诗》这样较标准的西方奏鸣曲式,亦有《春江花月夜》较为传统的音乐结构,还有《春颂》《刮大风》等以不同元素作为核心结构力的作品。作曲家不再拘泥于形式与技法,而是在全面掌握当代创作技法的基础上,以民族管弦乐特有的音响体系来表达多元的音乐观念。就整场音乐会而言,在如何更好地发挥民族管弦乐的音响优势方面也存在一些共识。例如,由于中国音乐旋律中细腻的润腔是艺术的精髓所在,乐队合奏不易统一而整齐地表现充满个性与精细的音高变化,因此,强调不同声部、组别或乐器独奏对旋律的展示与情感的抒发。其次,充分发挥传统音乐中吹打乐、锣鼓乐及其复杂的节奏体系特征,这也是本场音乐会乐队表演中最具现场感染力的因素。再次,对不协和音程及非传统功能和声的探索与开发,使之更适合民族管弦乐音响规律。
阎惠昌是新中国第一代经过音乐院校作曲和指挥系统训练的专业民乐指挥家,长期担任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民乐指挥家之一。他对于民族管弦乐的乐器属性与建制、音高律制、乐队训练、民乐发展理念等多个方面都有着独到见解。就本场音乐会而言,阎惠昌根据乐曲风格与特征进行乐器声部位置与配制的调整,将胡琴组置于舞台外侧,左侧是高胡、中胡声部,右侧是整个二胡声部,弹拨组放置在舞台中心,形成弓弦乐、弹拨乐、吹管乐、打击乐从外到内的声部结构,清晰地区分声部功能,使音乐会中几首乐器编配宏大的乐曲在音响呈现时层次清晰、主次有别,点、线、面不同乐器的音色特征融合而立体,避免了因乐队编制过大而出现的音响上的混杂,展现了其对乐队声音组合及配置精准的掌控。
北京民族乐团正式成立于2015年,隶属于北京演艺集团,前身是北京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相较而言,一个仅成立九年的乐团尚且“年轻”,但这也成为其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有利条件,年轻化和专业化更是这个乐团最显著的特征。乐团积极寻求与国内顶级指挥的合作,以从不同指挥家身上学习其成功的经验,帮助乐团迅速成长。本场音乐会正是这一实践的体现。乐团成立之初即邀约指挥家阎惠昌,后又搁置于三年疫情,终于在今年完成了与阎惠昌指挥的首次合作。演出当晚,北京民族乐团团长武旭海向阎惠昌颁发聘书,特聘其作为终身名誉顾问。就本场音乐会呈现出的艺术效果而言,经短短九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与发展,年轻活力的北京民族乐团已跻身顶级民族管弦乐团之列。
结语
什么是中国民族管弦乐的春天意象?本场音乐会给了我们答案。这里有云淡风轻与诗情画意,亦有深沉厚重及对历史、文化、社会的人文反思与生命情感的释义,是中国人以当代审美对春天及世界的认知与表达,展现了民族管弦乐创作积累的厚度与高度和指挥、乐队表演艺术的精湛与成熟。
中国民族管弦乐始于对传统的移植与西方的模仿,经一代代艺术家继承、融合与创新,逐渐发展为独立、个性与多元的音乐体系。这个体系扎根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吸纳当代艺术观念与技术手段,使其既是对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同时又具有超越地方性与民族性,体现时代精神与国际视野的特征。中国民族管弦乐的春天意象也将成为人类音乐文化有关春天主题最灿烂的组成部分。
注释:
①梁茂春《实诚在胸臆笔墨著竹帛——纪念李焕之诞辰100周年》,《人民音乐》2019年第4期,第37-41页。
②张伯瑜《从世界音乐格局看保护中国传统音乐的必要性》,《音乐研究》2018年第3期,第44-50页。
[本文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社科重点项目)“传统器乐工尺谱套曲研究”(项目编号:SZ202310046021)、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传统器乐工尺谱套曲研究”(项目编号:22GJB020)的阶段成果]
(本文图片均为刘方摄)
王先艳 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
岳喆 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