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南丝竹音乐盛行于环太湖区域,其在杭州的历史与浙派古筝的代表人物王巽之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浦东地区音乐世家“沈氏家族”传人沈凤泉来杭州工作,在与长期合作伙伴宋景濂等浙江籍丝竹演奏家的艺术实践活动中形成江南丝竹音乐在当代杭州的主要发展脉络。江南丝竹音乐在杭州的发展有其特点,在流传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疑点。沈凤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南丝竹”代表性传人,对这些问题都有较为长期、深入的思考,并对江南丝竹音乐在杭州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江南丝竹音乐;沈凤泉;风格;流派
采访时间:2022年11月
采访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沈凤泉寓所
受访者:沈凤泉,国家一级演奏员,著名二胡教育家、江南丝竹演奏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南丝竹音乐”代表性传承人,下文简称“沈”。
访问者:梁伟,浙江音乐学院副教授,浙江省音协二胡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江南丝竹传承教学研究”课题负责人,下文简称“梁”。
梁:沈老师您好!今天想就与江南丝竹相关的一些问题向您请教。
沈:我能回答的也不一定是对的,都是独家的意见,因为我的好多文章都是自己的一种看法,因为这个乐种啊,在50年代前都是自生自灭在流传,所以它没有什么专业的指导性文章,在50年代初期,杨荫浏先生有一篇文章《从“春江花月夜”的标题谈起》,这是第一篇文章。江南丝竹音乐在传承过程中既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艺术财产,也有很多的误传。
梁:还存在许多研究方面的空白……
沈:对,很多空白,现在我也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做梳理工作,希望能够矫正它。
一、关于江南丝竹音乐在杭州的传承
梁:我首先想要了解的是,在我们杭州地区,江南丝竹音乐的渊源与传承历史有很多不够清晰的地方,甚至如您刚才所说存在许多的误传。在您的书上提到:在20世纪20年代,王巽之所开创的“杭州国乐社”擅长演奏弦索十三套及一些江南丝竹乐曲,如《小霓裳》《灯月交辉》《高山流水》等[1]。那么在这之后江南丝竹在杭州的流传情况,您是否有所了解?
沈:杭州的江南丝竹代表人物在王巽之以后就是宋景濂和我,其他好像就没有了。
梁:这样就到了20世纪50年代了,因为您是1958年到的杭州?
沈:是的,在我来杭州之前,王巽之在三四十年代已经回到了上海,他将这些乐曲也带到了上海,比如《灯月交辉》,我们浙江的演奏在传统上都是弹拨乐的,作为丝竹乐传到上海以后就加入了二胡、笛子等乐器。
梁:您在上海时期有没有接触过王巽之的这些作品?
沈:没有,当时还没有,1956年上音(上海音乐学院)成立民乐系,我是第一届学生,师从陆修棠老师,那时候,王巽之还不是上音的老师,所以那时候对他还不了解,直到1982年我在整理杭州江南丝竹乐曲的时候收入《小霓裳》这首作品,也在此次谈到了王巽之先生与这首作品的渊源。
梁:所以杭州的江南丝竹乐曲在王巽之去上海之后还有人演奏吗?
沈:《小霓裳》还是有在演奏的,我来杭州之后就听到了宋景濂的演奏,他也给过我这首乐曲的手抄本,我看过以后,感觉这个记录是不大准确的,所以重新进行了整理,比如乐曲一开始,唱“la~sol sol”是从强拍开始的,但实际上应该是从弱拍上开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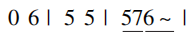 ,“la”应该是从2/4拍第二拍开始。中间也有一部分调整了节奏,最后,王巽之先生在结尾的时候是在本调上的,我把它搞了个微转,把最后一句的“mi sol la do sol~”改成了“fa sol la do sol~”,这是我改的,这样就感觉到了下属调,杭州后来演奏这首乐曲都按照我改的这个版本来。所以目前来说,这首来自于杭州民间的乐曲《小霓裳》,是由王巽之先生移植,由我来整理的。
,“la”应该是从2/4拍第二拍开始。中间也有一部分调整了节奏,最后,王巽之先生在结尾的时候是在本调上的,我把它搞了个微转,把最后一句的“mi sol la do sol~”改成了“fa sol la do sol~”,这是我改的,这样就感觉到了下属调,杭州后来演奏这首乐曲都按照我改的这个版本来。所以目前来说,这首来自于杭州民间的乐曲《小霓裳》,是由王巽之先生移植,由我来整理的。
梁:《灯月交辉》也是这种情况吗?
沈:《灯月交辉》也是的,这首作品出现比较晚,在1983年杭州地区演奏时还是用弹拨乐的,近几年,我把它改编成了江南丝竹的演奏形式。
梁:所以杭州地区江南丝竹的快速发展是从您来浙江工作以后开始的?
沈:我1958年来杭州后,碰到宋景濂,两个人比较合拍,他来自湖州的江南丝竹音乐世家,所以他的笛子吹出来全是江南丝竹的味道,因为我们这个乐种流传在杭嘉湖地区,它是有历史渊源的。我从小成长在上海浦东的清音班里,所以我们两个一拍即合,开始两个人不晓得相互的音乐风格,后来一听,都感觉江南丝竹味道很地道。之后队伍慢慢扩大。
梁:您来到杭州之后,杭州民间的江南丝竹传承是怎样的?
沈:杭州最典型的就是音协(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下面有个丝竹社,成立了“西子江南丝竹演奏团”,他们由一些退休的老师、演奏员组成,如厉行佳、曹筱红,他们专门演奏“浙派”的江南丝竹音乐。还有就是“金朝晖”丝竹社,以沈惠民、顾俊老师为主,坚持了非常传统的江南丝竹演奏。保持纯粹的传统丝竹也是对的,这是江南丝竹音乐的一个窗口,世界各地的人都想听你传统的草根艺术,不是听你的创作艺术,想要了解这个乐种的人们都想听到最真实的声音。我的想法和他们有一点不同,就是既要继承传统又要有所发展。
二、关于江南丝竹音乐的创新与发展
梁:我感觉您是很鼓励创新的。
沈:我嘛,肯定是要创新的。创新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传统的演奏,我将二胡上的演奏技法都用了进去,比方我改编《慢三六》,将跳弓都用了进去。江南丝竹的传统风格没有变,但听起来又有不同。在乐曲结构方面也都有改变,传统《慢三六》过于冗长,我在音乐的快慢强弱、艺术处理上都加以提升,更适合舞台上的演奏。其它的《春江花月夜》《紫竹调》都改编为江南丝竹,在舞台上演奏,大家一听都觉得很好听,这也是发展。一首作品是否成功,不在于比赛中是否得金奖、银奖、铜奖,真正的评委是坐在下面的人民大众。传统江南丝竹音乐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不是作曲家“创作”出来的。《慢三六》让人听起来还是那个《慢三六》,但“删繁就简”,把精华全部集中起来,原曲太长,演奏起来要十几分钟,现在只要五分钟,包括二胡的各种装饰手法—压弦、揉弦,都放了进去,这样才能“健康发展”。现在很多创作出来的江南丝竹合奏曲都在“同质化”,“基因”都转了,仅仅有些江南丝竹的音调在里面,如此下去,我们的后代恐怕都弄不清楚真正的江南丝竹是什么了。
梁:您觉得目前江南丝竹在杭州的发展是否也存在相同的问题?
沈:我对我们的“西子江南丝竹演奏团”一直强调,一定要“守本传承”,我们要抓牢几个典型团队,其它还有黄龙洞,还要进校园。
梁:现在杭州“黄龙洞”景区还有江南丝竹演奏吗?
沈:有的有的,不在露天舞台了,它里面有个音乐厅,打的还是江南丝竹的牌子,厉行佳在给他们排练,我有时候过去看看,也给他们讲,你们不是娱乐娱乐的,你们是给世界介绍江南丝竹的一个窗口。黄龙洞演奏江南丝竹是很有传统的,(翻出手机照片)这是1985年的演奏,周大风、李陵他们都在。后来2003年,写《江南丝竹音乐大成》的时候,李民雄来,我带他们去听,啊呀,全走样了,很可惜。后来,我要求他们一定要背谱演奏,丝竹音乐要想灵活起来,一定不能死谱演奏,要长期熏陶才能活学活用。
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学习江南丝竹音乐时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沈:共性就是江南丝竹音乐的整体特点嘛,个性的话,就需要江南丝竹中存在不同流派,所谓百花齐放嘛,就像武功各大流派,共性是都讲究“气”,但各个门派发展之后就有了差别。音乐也是这个问题,个性化是流派形成的基础。
梁:您觉得浙江与上海地区流传的江南丝竹有什么不同?
沈:这个要听,一听就听出来了,外行听就像两首曲子,内行听,能听出来是一首曲子,但风格不一样。具体讲,不是在主干音上,我将传统江南丝竹乐曲中的乐音分为主干音、支干音与加花音这三种。主干音是框架,不好动的,但加花音完全是个性化的,每个乐器的个性不同,走向也不同。上海同我们的不可能一样。没有个性化,就很难发展了。
梁:这对高校教学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不太有将学生送到地道的江南丝竹团体中长期熏陶、让他们自己体会的机会。
沈:还需要长期磨合。我同宋景濂两个人就是长期磨合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演奏风格。笛子、二胡能够代表这个乐种的演奏技术、风格。《行街》是比较明快的乐曲,以笛子为主;文曲如《中花六板》就以二胡为主,不用笛子,用箫,听起来有那种“糯”的感觉。我找来你听听,《中花六板》(翻手机),我演奏,老宋吹箫的,这是83年录的。
(放录音)
梁:所以您到杭州以后,您的江南丝竹演奏风格发生了哪些改变?
沈:那改变多了!我的立足点是“守本传承”,我认为“传承”本身就是动态的,所谓“活体”—人来做传承,一定是动态的,传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发展的过程,但是要健康发展。在传承过程中往往是泥沙俱下,各种打着“江南丝竹”旗号的演奏花样繁多、各种“江南丝竹”比赛目不暇接,这种金字招牌都贴上去后,这些曲子是不是江南丝竹音乐,要打个问号啊。
梁:这样的演奏,像您说的那个“本”还在不在?
沈:说在,好像有一点,像是贴花一样,还是按照一些传统的写作逻辑,起承转合啦,江南丝竹乐曲传承下来……江南丝竹音乐发展过程有它自己的一套规律,不是简单套用一些“模版”可以解决的,这是一种提炼的过程,是每一代乐人智慧的聚集,所以那些名曲也都是没有作者的,所以上海人说是“白相”出来的,就是“玩儿”出来的。玩儿着不好听就不要了,好听就加进来。
梁:它虽然没有明确的作者,但是一种集体的选择,在玩儿的过程中,越弄越好听。那么,您觉得江南丝竹的“本”在哪里?
沈:就是传统啊,根啊,流传到现在六百多年了,就在我们长三角地区,这个地区的人文、历史、语言、声腔就反映在我们民间的传统音乐里。所以江南丝竹的音乐特点不是几个字能概括的,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地域烙印,所以沪剧里面演奏的一些装饰手法也都是江南丝竹里面的,包括越剧、评弹、昆曲等都有江南丝竹的印迹,传统的吴越文化圈也就在长三角地区。有人说,江南丝竹发源于江苏太仓,我认为不妥,因为这是整体地域性的,不是哪个县、哪个市、哪个人所能独创的。例如,有说太仓张野堂搞出丝竹音乐,他是河北人,后来充军到太仓,与魏良辅一起搞昆曲,他作为北曲音乐家,同江南音乐文化相结合,搞出的清音,我个人感觉不好听,不如苏州的好听。
三、关于江南丝竹音乐的特点
梁:人们一谈到江南丝竹的特点就是“小细清雅”之类的……
沈:特点不是几个字可以说得清的,金祖礼也没这么总结,他说江南丝竹音乐的色彩、情趣可以说是“小细清雅”,但是也不全面。江南丝竹可以这么总结,那么广东音乐呢?可不可以也这么说?如果是共性的,描述性质的,就没什么意义。我分析这四个字,就是两个内容:一是形式,乐队的形式是小的,丝竹乐队都不大的;二是“情趣”,演奏与欣赏的情趣。我觉得,如果要鉴定江南丝竹要看四个方面:一个地域,一个代表性乐曲,还有一个主奏乐器的形成,另外一个就是装饰特点。
梁:我们现在讲江南丝竹音乐特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地域文化,江南丝竹的地域烙印就在长三角地区。您50年代后期来到浙江工作,之后长期工作、生活在杭州,您认为您的江南丝竹音乐风格与上海其它地区的江南丝竹风格在演奏方面有哪些不同?
沈:我从小在上海浦东农村里的丝竹音乐、清音班里成长,上海现在的丝竹音乐基本是城市里厢,上海城隍庙一带的丝竹音乐。我的演奏与现在以周浩为代表的上海江南丝竹音乐,曲子一样,但听起来差别很大。
梁:以前浦东的“清音班”也常常参加各种民俗活动吧?
沈:对的,一般都是婚庆活动。丧事用伴奏里面有“鹤器”的乐队。
梁:鹤器?是指唢呐吗?
沈:对,因为这个唢呐演奏时喇叭都是朝天的,像鹤一样,比较响亮,他们也演奏一些江南丝竹乐曲,但他们都是收费的。我们这个清音班是不收费的,完全是客串性质的,叫清客串嘛。我们说“清音”是乐种,“清客串”就像是“票友”性质的一种音乐表演形式,“清”是指“清音班”,“客串”就是业余参加一些婚庆、庙会这种活动。
梁:同样都是清音班出身,您的演奏与周浩先生在装饰手法方面也有很多不同。
沈:曲子都是一样的,要合也合得起来,但各种装饰音的区别就很大,在装饰音上的叫法也有不同,上下滑音、前后滑音、单倚音、双倚音甚至三倚音,有一些习惯性的说法,我们现在一般都采用比较规范、常用的音乐术语来表示。
梁:同样的江南丝竹乐曲,随着采用装饰手法的不同,在听觉上也会有很大的区别,例如陈永禄演奏的《中花六板》版本就和您的演奏多有不同。
沈:不一样的,我与周浩演奏的也不一样。我现在在思考江南丝竹音乐学派形成的基础是什么?不是在主干音上,而是在加花音的装饰、走向上的区别,也就是个性不一样,例如老六板的“mimilaredo”都是一样的,但是它放慢加花后的走向不一样,还有它的装饰手法不一样,有很多个性化的演奏方法。
梁:我们去学习音乐,对它内部结构细节的研究是很必要的。学生写论文分析作品,往往是为了分析而分析,我说你们研究这个作品的意义是什么?解决什么问题?研究的核心是什么?他们往往说不清楚。
沈:开研讨会一定要具体,不能泛泛地谈,否则最后大家聚个会,没什么结果。我当老师,我的主业是二胡教学,不是江南丝竹,江南丝竹是我的祖业。我一开始也不注意这个问题。我退休以后,二胡教学放到次要位置,就将对江南丝竹音乐的深入思考推到了主要地位。国家给我一个江南丝竹音乐传承人的名头,我就不得不投入到其中,最近一二十年一直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四、关于江南丝竹音乐在流传过程中的一些疑点
梁:之前也听您提过,说浙江江南丝竹音乐流传于“浙西”,应该是不对的?
沈:我之前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杭嘉湖在浙北地区,浙西主要是衢州地区。最早上海的老专家在整理江南丝竹音乐的时候,他们对浙江各个地区的地理方位不太弄得清,之后《中国音乐词典》采纳了这种说法,说浙江省江南丝竹流传在浙西[2],它的根源是1958年有篇文章说上海的民间丝竹音乐逐渐流传到了浙西……但是浙江东西南北各有不同的音乐文化,浙东的丝竹乐中有首《文将军》,和我们江南丝竹完全不同;浙南温州地区的丝竹乐是在“莲花落”基础上形成的,也与我们的音乐差距很大;浙西的婺剧音乐是它的典型代表,例如赵松庭演奏的《三五七》……
梁:现在还是能在一些对江南丝竹的介绍以及普及类文章中看到这种说法,所以词典上的不准确对其后会造成很大影响。我们现在所说的“江南丝竹”的传统流传地区还是在长江中下游的环太湖区域。
沈:是这样的。还有,江南丝竹八大曲,也不能说错,只是在江南丝竹传统作品流传过程中有点传歪掉了。例如《中花六板》,来自于《老八板》《老六板》,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乐曲,也有人把它叫做《熏风曲》。“八大曲”这种提法其实并不全面,我们老前辈金祖礼从没讲过“江南丝竹八大曲”,他只说“所谓江南丝竹八大曲”,我们在编写《江南丝竹音乐大成》[3]的时候,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江南丝竹八大曲”能不能提?这只是历史上曾有的一种说法。在四十年代初,日伪时期,上海搞绥靖政策,要安抚老百姓,不要反抗,表现出“莺歌燕舞”的生活状态,粉饰太平嘛,所以在“新世界”里设有“丝竹游艺场”,也是为帮助敌伪宣传,所以挂了八个牌子,《三六》和《慢三六》,《中花六板》《慢六板》,《四合如意》《行街》,《欢乐歌》和《云庆》,这是很内行的人选的。这八块牌子怎么用呢?就是有人会这个曲子的,就拿下这个牌子往桌子上一放,不要报幕的,玩儿嘛,演奏完再放回去。这样传下来,所以在我们民间是没有江南丝竹大曲、小曲之类说法的,只有“大套”,套曲,像是《春江花月夜》。
梁:传统上还有叫“五代同堂”的套曲,从《老六板》开始,《花六板》《中花六板》《慢六板》《快花六板》这样演一大套。江南丝竹还有许多经典乐曲,像是《江南丝竹音乐大成》中收集到的流行于上海、江苏、浙江的江南丝竹有将近150首,江南丝竹如果只重视这八首,就会产生排他性,这些经典曲目有它的代表性,但也有局限,其它还有像《春江花月夜》《小霓裳》等许多经典的江南丝竹乐曲。还有就是对江南丝竹乐曲的命名问题?
沈:作为江南丝竹乐曲代表曲目之一的《中花六板》,是我们祖宗起的,大家所公认的。李芳园的琵琶曲有首叫《虞舜熏风操》,也是用老八板的曲调,后人附会,将同样由老六板、老八板发展而来的《中花六板》也称作《熏风曲》,所以到了20世纪40年代,出了所谓的“八大曲”,第一首曲子就叫《熏风曲》。和它相似的《三六》也被改名为《梅花三弄》,这个与古琴曲的《梅花三弄》是同样的乐曲吗?一听完全不一样啊!这就产生很多误解。这样本来是无标题音乐的民间乐曲就变成了标题音乐。我把这种《三六》《中花六板》都叫做“数字标题音乐”,这种“数字标题音乐”最大的特点就是随着乐曲情绪变化以及演奏场合的不同,它可以长也可以短,可以个性化地演奏。所以我提出来,世界上有标题音乐,有无标题音乐,其实在我们民间音乐还存在一种“数字标题音乐”,戏曲里也有,在婺剧里有慢板、中板、快板的“三五七”,每种情绪都不一样。后来赵松庭把它改为笛子独奏曲《三五七》。我还讲过,“江南丝竹”这个名字有缺陷。这种讲法从什么时候出现的?
梁:这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上海成立的“上海市国乐团体联谊会”演出活动后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
沈:我最近在讲学中也提到,什么是约定俗成?约定俗成是有一定范围的,最小是两个人、一个家庭,再到一个地区……出了这个区域人们就不承认了,嘉定里厢,儿子叫阿狗,女儿叫阿猫,你家里晓得是这样,离开嘉定这个圈子以外,人家就不晓得你说“阿狗”是谁了(笑)。所以“约定俗成”要有一个范围的。现在我们江南丝竹音乐这个乐种是面对世界的。我老举一个例子,我们浙江江南丝竹去全国巡回演出,在天津电子仪表厂,饭厅外贴个广告,今天晚上江南丝竹活动,结果,来吃饭的人议论:这是啥东西呢?是去做手工?
梁:(笑),还是研究纺丝伐竹?
沈:我想这是什么问题,不是他们无知,而是我们这个提法缺少“属性”,如果叫“江南丝竹音乐”,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原来都叫“清音”—“江南清音”,这就不会错。这个名字其实也很好,有明确的针对性,不会有歧义。据我考证,“清音”的历史从殷商时期就开始了;到晋朝,“丝竹清音”这个名称已经开始流行了;后来,到了唐代,“清音”还是个宽泛的音乐概念,没有伴奏的歌唱,叫“清音”,没有吹打的器乐合奏,叫丝竹“清音”;宋代以后,逐渐地,“清音”这种叫法成为长三角地区民间丝竹音乐的代称;到明代就更加确定了长三角地区的民间音乐就叫“清音”。一直到现在,我们浦东还是叫“清音”,演奏班子还是叫“清音班”,叫他们改为“江南丝竹班”,他们改吗?不肯的,毛别扭的,叫“清音”就毛亲切的,我沈凤泉从小在清音班长大,这个名称多少好啦,什么叫“清音”?天籁之音啊,就是最好听的声音。
梁:这个名称不但有很久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有很好的寓意,值得我们对它的历史发展与文化涵义做更深入的研究与界定。包括“清客串”这种说法,也就是演奏“清音”的这个班子,以“客串”的形式,业余的、非营利性的形式,参加一些像婚庆等民俗活动。
沈:对的,就是这个概念。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亲身经历过,知道一些,像我儿女这一辈的,也不清楚,要讲给他们听的,这也是传承。我们之前编写《江南丝竹音乐大成》,讨论书名是《江南丝竹大成》还是《江南丝竹音乐大成》,我是第一个发言的,一定要用《江南丝竹音乐大成》,口头上可以,口头上再省略叫“丝竹”都可以,但落实到书名上不行。
五、总结与一些希望
梁:您觉得对您的音乐生涯影响最大的事情或者人物是?
沈:我的叔父是影响我一生的,我的叔父弓弦乐器都演奏,是演奏江南丝竹的高手,他一直带我成长。到了上海音乐学院是陆修棠,所以我又是民间又是专业,到了浙江就是同宋景濂合作,长期以来,形成了浙派江南丝竹的基础。曾有记者问我,浙江的江南丝竹音乐特点是什么?我说一句话,混血儿。我是浦东过来的,宋景濂是浙江湖州的,我们两人配合,就形成与两边都不同的一些特点,《中花六板》就很典型,他演奏的箫的特点就和上海的演奏不同,但很难用语言表达,它太灵活了。
梁:您对我们很多有志于学习江南丝竹的学子有哪些忠告和期望呢?
沈:我希望我演奏的二胡可以在浙江很好地留下来,所以我2016年、2019年两年在桐庐办了传承班,邀请陆春龄、周浩,还有我,将我们省内的二胡江南丝竹专业演奏者都集中在一起学习,吃住在一起,开心。要有愿意学的学生过来,不是口头上学两节课,一定要有成绩能够反映出来。技巧不是很难,但是韵味很难掌握,首先要有愿望,之后也不能局限于简单模仿,要活起来,学习传统的演奏意识以及演奏手法,这就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了。
梁:所以,一方面对江南丝竹音乐传承的要求很迫切;另一方面,对江南丝竹音乐的学习又急不得。这两种状况在相互牵扯。很希望您可以把年轻一辈带出来。
沈:我很希望这样,上海有我儿子女儿了,浙江还不行唉,还是没有真正到位,我想浙江音乐学院应该有这个乐种的传承平台。
梁:浙江音乐学院国乐系目前在研究生教学层次开展了“江南丝竹研读与演奏”课程,希望能够依托这个教学平台,请您多多过去指导。
沈:好!要有固定的老师,不能流动性太大。特别是四大件—二胡、笛子、琵琶、扬琴一定要有稳定的师资,要排练《中花六板》《欢乐歌》这种传统作品,打造传统民间音乐的牌子。
梁:谢谢沈老师,今天聊了很多,收获很多,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机会向您请教。
参考文献:
[1]沈凤泉.沈凤泉江南丝竹音乐艺术[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118.
[2]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中国音乐词典[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365.
[3]李民雄.江南丝竹音乐大成[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