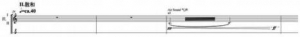《琴况二则》是贾国平于2021年完成的一部管弦乐作品,首演于2021年12月4日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办的“和乐中西融创未来”音乐会。这部作品由2021年11月完成的《太和》篇与1998年创作、2021年重新编配的《清调》篇组成。《琴况二则》的诞生基于作者对明末徐上瀛所作《溪山琴况》的解读,以及对古琴音乐的感悟。《溪山琴况》可以说是中国古琴音乐美学和古琴表演实践理论的集大成者,其对古琴艺术提出的“二十四况”,至今都是古琴音乐极为重要的审美范畴。作曲家对《溪山琴况》的深刻认知最终外化为声音,用管弦形式重新诠释了《溪山琴况》中“和”“清”二则。
无疑,这部作品是一次个人美学境界与现代作曲技法的完美融合,而作曲家对中国审美韵味和文人精神的追求早在1998年的《清调》中就已有展露。这首创作于作曲家德国留学期间的《清调》,就源于对“如何用中国文化和音乐传统创作新作品”的思考。对比1998年与2021年两版《清调》,最大的改变不在于音响的变化,而是跨越20年后作者对古琴意蕴认识的改变——化有形于无形,在无形中处处显形。
1998年创作的《清调》是为管弦乐队与录音磁带所作的,古琴的声音以录音带方式保留了下来。正如作者在当年的作品介绍中说的那样,他希望乐队成为古琴的一种延伸。而2021版的《清调》则取消了这些录音片段,将原先的古琴旋律完全融入管弦乐,但整体音乐效果仍不乏古琴韵味。在《太和》这篇新作中则将无形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在《清调》中还能找寻到古琴音调的吉光片羽,那么在《太和》中更多的则是感受到古琴艺术的意蕴,无需去捕捉古琴的影子,而是作者对古琴的感悟。《太和》分为和鸣(巍巍山高)、散和、太和(洋洋水碧)三大部分,作者以“和况”中“和”的三种形态串联整个作品,听后令人顿悟陶渊明的“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此曲中“无琴”亦“无琴声”,但又何尝不是处处有出“琴意”,句句有“琴声”。
听完这首作品后,除令人含商咀徵回味无穷之外,也不禁引起一些思考:一方面透过这首作品我们可以一窥,当代专业音乐创作是如何运用现代音乐创作方式来呈现古琴中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更进一步讲,以古琴为代表的中国审美、文人精神是如何在当代专业创作中聚焦的;另一方面,更为难得的是,在这首跨越二十多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以贾国平为代表的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中坚力量对中国当代音乐的认知与审美的转变。
从音乐形式上来看,《琴况二则》使用了管弦乐的形式和20世纪无调性现代作曲技法,但实质却以中国审美意趣、文人音乐精神和古琴音乐审美为核心。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作曲家在创作思维和审美观念上的两层转变,将中国审美意趣在看似西方的管弦乐形式中充分呈现,摆脱纯粹对古琴音效的模仿,以现代的作曲技法和音响手段表现出他所领悟的古琴意蕴,真正从美学、文化的深度展现古琴艺术的“弦外之音”。
一、超越中西范式追寻自我语言
《琴况二则》采用“管弦乐”形式。在中国当代创作语境中,“管弦乐”对于创作者来说,越来越回归其“器”的属性,与之相随的是一种更加包容、多元的审美民族性凸显出来。这种当代的审美民族性不再以是否采用某种民族乐器或特征音调为民族性标志,而是以更深层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内涵来界定。《琴况二则》,尤其是其中的《清调》一篇,由1998年版发展到2021年修订版,很好地展现出中国作曲家从早期注重将中国音乐元素加入到现代作曲技法之中,到当下以表现中国审美意趣为核心的这一观念上的转变。
《清调》中的录音带记录了琴曲《广陵散》的一些曲调,并将这些片段式的要素分散在全曲七个章节里。2021年版的《清调》则放弃了录音带,而是把这些曾记录在录音带中的曲调分散在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钢琴、竖琴中,并采用拨弦、滑音、打音等形式模拟古琴音色。这其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转变,那就是作者不再将管弦乐视为一种带有欧洲民族属性的标志,而只将其视为乐器,一种承载并表现作曲家赋予作品审美意趣的装置。1998年版《清调》将磁带录音与乐队结合,无疑也是将民族韵味与现代音乐相结合的一种尝试,并且更直接地展现出了古琴本身的音色,但其中也带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潮音乐”的一些特点,如较直接地加入中国音乐元素。虽然磁带录音的古琴音乐更加直观的让人们与中国音乐、古琴音乐联系起来,但反过来其实也是将整个乐队与被录音的古琴音乐从心理上产生对峙。被录音的古琴曲调,除起到音色上的融合、展现那个时代对于录音电子艺术的运用之外,其实也在提醒听众,这里运用了中国音乐元素。当音乐的接受者感知到这些信号时,就会下意识地在欣赏作品过程中寻找录音带中的古琴曲调,当然也可能忽视整个作品的完整性和乐队中所蕴含的更丰富的中国音乐审美意趣。
2021年版的《清调》,将曾靠录音展示的曲调元素分配到各个声部,并使其交响化,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模仿古琴的音响效果。例如,中提琴和大提琴就代替了原本录音的古琴音乐曲调,其中就有用滑音模仿出古琴的“吟猱”,用指甲拨弦模仿古琴弹拨时产生的甲声,以及用手指直接敲击琴弦打音模拟古琴以指肚发声的肉声或半甲半肉声(见谱例1)。但从整体的音响效果上看,2021年版的“古琴”音调完全融入管弦乐之中,也更符合贾国平化中国音乐曲调于无形的风格。
谱例1《清调》第63—66小节部分声部
这种对古琴音色的模仿可能得益于周文中《渔歌》中那种用管弦乐器表现古琴音色的方式,但又与《渔歌》中对于曲调的模仿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模仿的目的不是展示管弦乐器对东方音色再现的可能性,也不是为了用管弦乐再现某个古琴曲,更多的是以这种“薄雾蒙蒙隐见月”的拟态音色形成独特的中国音韵,表达一种东方的审美态度。贾国平在这首作品中的目的不是展现某种乐器对另一种音色的模拟,而在于以一种似真似幻的拟像勾起听者对古琴音乐、对中国音乐审美的意向。可以看到,这些古琴曲调元素被作者安插在各声部之后,似乎没有像录音带那般直接惹眼,但却真正与整个乐队融合,乐队不再是由单一的乐器叠加,而是真正融合为一个整体,每一个突出的部分都成为这个整体的延伸,这也是贾国平独特的音乐语言之一。
这种将管弦乐队融合为一体,形成一种交织音色的方式在《太和》篇更加明显。开篇第一个和音就将听者拉入一个宏大、立体的音响结构之中。就如开篇标题“和鸣(巍巍山高)”所述一般,丰满的音响效果融合着所有乐器共鸣产生的音色,在力度的缓缓流动间展开一卷写意山水的画卷。“和”蕴含着“杂多”而“统一”之意,而管弦乐队融合性反而最适合将复杂的音色统一起来。在《太和》尤其“和鸣”这部分,几乎没有哪一件乐器可以完全独立在整体音效之外,作曲家将整个乐队一体化,一方面以饱满丰富的音色表现巍巍高山之感,同时也展现出一种得之于“二十四琴况”之“和”的文化包容性。
二、突出“个体性”,以审美构建精神共鸣
如果说《清调》1998版到2021版的转变,所展现的是以贾国平为代表的一批“60后”作曲家在对待“中西”文化和审美观念上的转变,那么2021年的《太和》则彰显出对创作技术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一种更加深层次的思考和个性化表达。
其中,《清调》完整保留下了1998年版的结构和技法,如其中的十二音技术与序列写作思维,而《太和》的音高结构则完全来自五声音阶思维的扩展。《清调》中的作曲技法,或多或少受到“集合理论”的影响。尽管这一时期的创作已在各种现代作曲技法上展现出强劲的实力,并有许多作品对中国音乐融入现代音乐创作进行了各种尝试,但这一时期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对技术的实践和探索。与之相比,《太和》篇则似乎以一种更加简洁的思维方式展现出了更丰富的音乐效果。
《太和》似乎都是五声性思维的纵向、横向拓展。开篇以(C-G-D-A-E-B-F-C)一个五度叠置的宏大纵向和声,和横向不断强调的小三度与大二度音程关系直接将听者带入中国音乐氛围之中。与纯粹的五声性运用不同,作品在五声调性游移和调性并置中呈现出斑斓的音响色彩。
在《太和》“散和”的开始部分,仅用几个音就将虚、实、散展现出来了,表现出中国音乐“形散而神不散”的审美特征。泛音和不静止的自然延音与其说在模仿古琴音色,还不如说是在表现古琴的神韵。如谱例2、谱例3所示,打击乐、弦乐和竖琴的点状散音,与长笛似有若无的气声音响形成虚实对比。
谱例2《太和》第29—31小节长笛声部
谱例3《太和》第29—32小节部分声部
当下,作曲家们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理解正在发生转变。从技术的学习运用,同时加入中国音乐元素,到将技术作为艺术挥洒自如地运用到作品之中,以游移的调性、变化的律动和自由的旋律等现代音乐技术思维表现某种特定的带有中国审美意味的意向性内核。这也是作曲家们寻求“个体性”的一个关键。
在中国音乐审美意趣中寻找精神内核,是贾国平音乐创作的重要审美取向。他的创作风格受中国传统艺术及和审美的影响,既有来自文人的音乐风骨,又有自成一系的音乐语言。《琴况二则》充分展现出这种个性与传统结合的特征,向听众展示出他所感悟的古琴审美况味。在《溪山琴况》的“二十四况”中,第一况“和”可以说是贯穿整部《溪山琴况》的核心审美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包含多层内涵的审美范畴。作曲家以《太和》开篇,以音乐这种特殊的“语言”表达作曲家个人的、不受外界干扰的对古琴乃至整个中国音乐审美况味的一种感悟。
“其所首重者,和也。”“和”应当说是整个《溪山琴况》中提纲挈领的审美范畴,包括其后的“静”“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和”的延续。清代苏璟《春草堂琴谱·鼓琴八则》就认为贯穿“二十四况”的精神可以用“清和”二字概括。《溪山琴况》中“和”的命题本身就是儒道两家的融合之物,既有“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多样统一思想,又有“大音希声”的道家思想。另外也围绕着“弦、指、音、意”之间的关系谈论“和”在古琴演奏中的层次。《太和》的三个部分对应着作曲家对“和”的解读,同时又以“其有得之弦外者,与山相映发,而巍巍影现;与水相涵濡,而洋洋徜恍”的审美观贯穿全曲。这首作品与其说是用音乐阐述对古琴音乐的理解,更像以音色写丹青,以音响展现写意山水。作曲家将其对《琴况》中“和”的理解化为音色,而以音色表现的则是这种审美意趣下的韵味和意境。
古琴音乐与其他中国传统器乐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中富含文人艺术韵味。在《太和》中,作者以不同的音色和音响效果表现这种韵味。这里可以简单地以停止演奏之后是否还能产生延音为标准,将本首作品中的乐器划分为两种:有共鸣乐器和无共鸣乐器。而在这两种共鸣同时产生时,弦乐器和管乐器需要依靠表演者持续演奏保持固定的音高,但打击乐、钢琴、竖琴在停止演奏之后可以产生自然的延音,而这个延音不再以固定的音高呈现,而与弦乐、管乐固定音高的音色相融合,产生一种惶惶壮阔而虚无边界之感,这也是古琴音乐中“滚拂”所产生的音响效果。另外,作曲家对打击乐的选择,全部是带有音高并且在声响上有延音和共振的乐器。这也让《太和》在听觉效果上多了一份黄钟大吕之感。
作曲家用似有若无的音响效果营造出一种虚实相生、留白与氤氲相间的审美境界。这体现在《太和》三个部分之间的衔接处,如在“和鸣”向“散和”过渡的一小节,全部乐器均为带有延长记号的全休止。在看似无声的状态中,其实还有前小节延音的余韵。本身这个休止小节就像水墨画中的留白,承接着画卷中的两个部分,但在这块留白中还若隐若现地呈现出水墨氤氲,不禁令人流连。在《太和》的结束部分使用了同样的方式,将这种氛围感从开始持续到乐曲终了。而“散和”向“太和”的过度则是由大提琴、低音提琴、打击乐构成一个音量微弱的背景层,竖琴刮奏出一条像涓涓细流一般的音流,引入下一部分“洋洋水碧”。这个过渡性小节中,明明有音,但音量越来越低的竖琴让人有一种消失感,反而产生一种实则而虚的感受。
《太和》的最后一个部分“太和”(洋洋水碧)以多声部大量的快速琶音音型让人极易联想到奔腾的河流。全曲以山开始以水收束,不由让人想起“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而这一静一动构成的音韵与意境又何尝不是“和”的真谛。
“清者,大雅之原本,而为声音之主宰。”作者所理解的“清调”,就在于清澈而纤细的旋律和音调。然而,《清调》从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干净与清透,作曲家采用了一种“单声思维下的多层次”陈述方式,“也就是说,乐谱表面上看似丰富的多声技法实际上就是单声思维下的产物”①。这种方式使得音乐在保持纵向发展时,也维持了横向听觉层面的线性逻辑。还值得关注的是,《清调》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全曲几乎没有相同的节奏,而作者这种规避使用相同的节奏的做法,直接形成了中国传统音乐中散拍子的音乐效果。这大概就是“节奏有迟速之辨”的雅趣。
透过《琴况二则》不难发现,作曲家视野的个性化,以及所展现出的中国古典审美思想以及文人古琴音乐神韵。他以各种细小的音色和音响构成了一个饱含中国韵味和意境的氛围,而在这种氛围之中,听众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作曲家预先营造好的“暗指”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可被感知的群体精神。正如斯克鲁顿所说的,“暗指是自动引入一种社会背景——共同的知识、共同的意指、共同的象征——这一切一起体现为一种共同的体验。通过理解一种暗指,我们开始最大限度地认识到意义体验所暗含的群体性”。“这里涉及‘文化’——社会背景、共同知识和共同体验。审美体验是一种社会群体行为,因此社会各方面的共同性,使音乐的暗指能够被社会群体理解,从而产生音乐的共享。”②尽管他认为这种“暗指”只能出现在调性音乐中并且是作曲家的有意而为,但在当下音乐创作和审美中,这个概念还是可以扩大的。一切出自艺术家对音乐审美、文化的解读,在精巧的现代音乐技术化的音响和音色中,都可以成为一种“暗指”。而通过审美活动,与作曲家有相同文化联系的审美者也会意会作曲家的“暗指”,从而产生精神共鸣。
《琴况二则》以《溪山琴况》作为文化基石,以古琴音乐为出发点,展现出更为广博丰富的中国音乐神韵,用音色和音响构建出一个充满浓郁中国色彩的立体音响空间,让听者沉浸于其中并逐渐感受作曲家赋予作品的审美内涵和文化意义。《琴况二则》是一首让人沉醉其中的中国当代音乐作品,以“管弦乐”这一特定体裁为表现形式,表达出古琴的神韵,展现出中国音乐的审美意趣。
①张巍、霍凡超《管弦乐Qing-Diao(清调)研究》,《黄钟》2021年第1期,第19页。
②转引自宋瑾《斯克鲁顿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