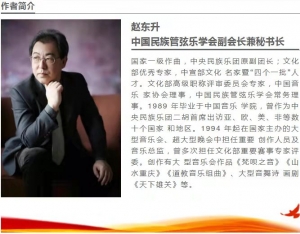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赵东升
中国民族器乐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彩。就大型编制的合奏形式来讲,从1920年“大同乐会”算起,中国近代职业化民族乐队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发展史。百年间,这类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表演主体,从最初的探索、创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扩充、改进,再到形成结构相对稳定、音效相对丰厚的民族管弦乐队,它映射着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轨迹和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时代印记。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文化的意义被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党和政府立足文化强国、强调“守正创新”,高度重视包括民族器乐在内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为我国文艺工作者的文艺创作、文化生产指明了总方向,提出了根本要求。
在优越的时代环境下,民族管弦乐的创作与表演进入新一轮的活跃期和发展期,各表演团体、作曲家、演奏家积极响应时代召唤,不断突破,苦心追求,创作出许多兼具艺术性、思想性和商业性的新作,这些新作在创作模式、表演方式、乐器组合、剧目结构等方方面面呈现出从单一到多元并存的发展态势。下面就我视野所及,对多元并存的发展态势谈一谈个人的认识。
一、主题性音乐会的大量涌现
主题性音乐会是指以一个明确的主题为中心架构而成的一整台音乐会。我们知道,传统模式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多以单个乐曲的形式创作与推出,传统模式的民族管弦乐音乐会也多是根据需要选取曲目、组合上演。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着力扶持、大力助推舞台艺术事业,诸如“国家艺术基金”、“文化和旅游部剧节目专项资助”、“全国舞台艺术创作精品剧目扶持”、“时代交响——中国交响音乐作品扶持计划”等作品创作扶持工程、优秀剧目孵化工程,催生了一大批主题性音乐会。例如,中央民族乐团创作推出的《丝绸之路》、《艰难辉煌》、《山水重庆》、《畅想京津冀》、《长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创作推出的《崛起》,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创作推出的《国之瑰宝》,北京民族乐团创作推出的《新国门畅想》、《燕京八景》、《大运河》,广东民族乐团创作推出的《丝路粤韵》,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创作推出的《丝路长安》、《永远的山丹丹》,浙江歌舞剧院创作推出的《富春山居图随想》,山西省歌舞剧院推出的《山西印象》,前卫文工团创作推出的《甲午·甲午》,河北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创作推出的《大河之北》,苏州民族交响乐团创作推出的《丝竹里的交响》,重庆民族乐团创作推出的《思君不见下渝州》等等。
梳理一系列主题性音乐作品,至少可以映射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较之以往,当今主题性音乐会更加注重思想性、整体性以及乐章(乐曲)之间的关联性。我们知道,作为音乐会形式的民乐呈现,在整体表达上的确逊于其他戏剧类舞台艺术品种,所以,我们并不要求每台音乐会都必须按戏剧作品那样以起因、发展、高潮、结局来表述一个故事,但是一台成功的音乐会,一定需要遵循某种逻辑关系来进行串联。换言之,一台完整的剧目需要整体布局,速度的快慢缓急、情绪的跌宕起伏、结构的起承转合等因素都应考虑其中。主题性的音乐会自然更注重整台剧目的逻辑、曲目与曲目之间的关联和线索,例如,民族管弦乐《丝路粤韵》以航海事件串陈主线,用【开海】【祭海】【远航】【异域】【乡愁】【归来】【新梦】七个乐章展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画卷,结构清晰、安排合理。又如,《思君不见下渝州》是以千年诗城重庆不同历史时期的著名诗篇用音乐的表达形式纵横于整台音乐会中,从而使诗词的文学美感与民族管弦乐的听觉美感达成和谐共振,诗与乐的内在关联让观众在时空转换中加深对古典美学的理解。除此之外,还有以年度周期为逻辑架构的民族管弦乐作品《高粱红了》,音乐会通过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为线索,折射出黑土地儿女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
第二,透过一系列主题性音乐会,可以更直观的反映文艺作品与时代的关系。“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们看到,在上述例举的主题音乐会中,大多紧扣重大时间节点和国家战略,比如围绕“一代一路”“中国梦”“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坚定文化自信”等重大题材的创作占比较多,反映出广大文艺工作者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责任和使命,反映出他们为中华民族的高光时刻留下华彩乐章的志向。
第三,许多主题剧目成为回归“集体创作”的实践基地。主题性剧目创作基本遵循两条路径,一条是将一台音乐会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委约一位作曲进行创作,另一条路径则是数位作曲围绕共同的主题进行的集体创作。从两种路径的创作作品来看,各自的优劣均较为明显,前者乐曲风格和布局相对统一,但容易出现乐曲的同质化;后者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让整场音乐会更为丰满,但不容易把握整体,可能出现亢奋点太多、高潮太密集、音响太满等现象。因此,如何在集体创作中解决“整体性和统一性”,成为当前主创团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相信随着时间与经验的积累,我们会在更多成功的案例中,不断总结激活“集体创作”的内在机制。
二、跨界融合剧目的探索发展
民乐的传统表演模式就是“音乐会”模式,不论编制大小,抑或乐器摆位各异,演奏者在固定席位上演奏乐器,观众在台下欣赏乐曲,无可非议,我们惯常的说法称作“听民乐”,而非“看民乐”。但进入新时代以来,打破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固定表演模式、将剧情引入民乐的方式成为许多创作者乐于尝试的新模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不少的民族乐团在守正创新方面屡屡有不凡的表现。2013年,中央民族乐团推出大型民族乐剧《印象国乐》,引起不小轰动。在《印象国乐》中,乐团打开延续近一个世纪的固定席位,运用行为艺术,通过舞美、灯光、服饰、多媒体、升降平移、起落伸缩的多功能舞台,把大家习惯成自然的音乐模式塑造成非同凡响的听觉并视觉冲击。这些赋予器乐文化立体感的现代气息,有效提升了观众对民乐的认识和喜爱。用现代网络流行语描述,《印象国乐》成功“跨界”,的的确确火了一把!之后《又见国乐》、《玄奘西行》接踵而至,以一股“引领性”的影响力,惊艳了国内外民族音乐院团,之后几年内,业界推出不少此类跨界合作的民乐作品。例如,上海音乐学院创作推出的民族器乐剧《笛韵天籁》、湖南省歌舞剧院推出的多媒体民乐剧《九歌》、广东音乐曲艺团创作推出的大型情景器乐剧《扬帆大湾梦》、重庆歌剧院创作推出的跨界多媒体舞台剧《大禹治水》、南京民族乐团创作推出的音乐剧场《桃花扇》、重庆民族乐团创作推出的情景音乐剧《告别千年》、北京民族乐团和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共同推出的音乐剧《刘天华》、中央民族乐团创作推出的民族音乐纪实剧《家园》等等。这些具有一定意义的创新作品无论业界怎样探讨和评价,其剧目本身这种融入多种元素的新型模式都以打破相与因循的传统形式而给人们留下深深的印记。
三、地域特色作品的多样呈现
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反应本土文化特征的作品占目前新创作品的绝大多数。“立足本土、吸纳优秀的民间文化”继而创作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的作品,这一准则也早就被作曲家们达成共识。但进入新时代以来,作品的在地化、多元化、特色化趋势尤为明显,这一趋势既有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对民族元素的应用,更有地方院团主动参与出品和创作的优秀成果,如果将前者比喻为“自上而下”,后者则可以看做是“自下而上”。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近年来“自下而上”的创作行为催生了一大批具有地域特色民乐作品,映射出整个创作环境的良性发展,也为创作者在深度和广度上拓宽了空间。在上文提到的很多主题性音乐会可以直观地反应出各地民族乐团在弘扬本土音乐文化上做出的多方努力,例如,《山西印象》(2015)、《山水重庆》(2016)、《大河之北》(2018)、《燕京八景》(2020)等等。有些作品,甚至打破民族管弦乐的固定编制,将地方乐器推上了主导地位,例如,贵州省花灯剧院创作推出了交互式民族音画《高原·听见贵州》(2018),该作品乐队使用的乐器是以瓢琴、牛腿琴、侗笛等贵州民族民间乐器进行改良的乐器;再如,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民乐团创作的民族管弦乐《蒙古马》大量使用马头琴、四胡、三弦、火不思、雅图噶、牛角号、布列号、毕秀固尔等蒙古族特色乐器。诸如此类的特色乐器组合作品,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这些新作品无不有着大胆探索、努力创新的精神,当然,我们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也需要清醒的地认识乐器改革仍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它应该纳入文化演进的过程,我们仍然需要在民族管弦乐队的演绎形式、音响平衡、乐器应用等方方面面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积累更丰厚的作品。
综上,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创作与发展将置身于越来越多元和广阔的生态空间,同时,也面临观众更加多元的审美需求,因此,作品的成功仍需要付出更艰辛的努力,需要在践行中不断积累,需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引导。
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对民族管弦乐事业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